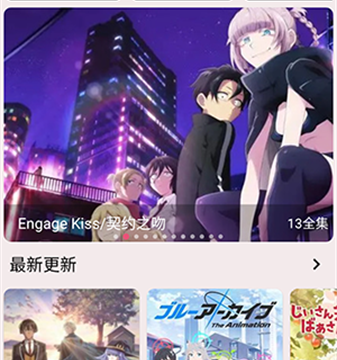在传统哲学史上,自伏羲提出八卦,文王演变为周易之后,人们便将周易固定下来,作为了真理性的学问。但其实,易学在发展过程中,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佛教哲学传人中国后,便与易学发生了相互影响,或以佛教哲学解说易理,或以易理解说佛教哲学,佛教与易学相互影响[[i]、[ii]、[iii]]。本文仅就佛教与易的相互影响作些粗浅的论述,不对之处请大家指正!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
佛教在传入之初,人们注意到佛教与易都具有巫术和道德教化,由此,佛易之间的互释便从巫术与道德方面开始。据现存史料文献记载,三国时的康僧会是已知的以易释佛的第一人。康僧会在吴国传教,吴帝不信佛法,问曰:“佛教所明,善恶报应,何者是耶?”康僧会在问答中有言:“《易》称积善有庆;《诗》咏:‘求福不回。’虽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训。”[[iv]]吴帝又问:“若然,则周孔已明,何用佛教?”康僧会回答:“周孔有言,略示近迹;至于释教,则备极幽微。故行恶则有地狱长苦,修善则有天宫永乐。举此以明劝沮,不亦人哉。”[[v]]康僧会在这里把佛教因果报应的观点与《易经》积善有庆、积恶有殃的思想沟通,是一种借易明佛的“权说”。
南北朝时期,入华僧人除利用西域奇物(如火浣布)和吞刀吐火等魔术来宣扬信佛后的神力外,还利用易卜作为传播佛教的手段。据史载,十六国时期的般若学大师鸠摩罗什,他不仅以望气巫术宣扬自己的超凡能力,而且以占卜之术闻名。《高僧传·卷二》说他:“博览《四国陀典》及五明诸论([外道经书]—— 高僧传注补),阴阳星算,莫不必尽,妙达吉凶,言若符契。”[5]自此之后,时至今日,在佛寺中抽签算卦也是一种平常风景。因为佛教在创立之初就是对巫术信仰的否定,所以稍后的僧人便批判了易卜,并借佛教哲学阐释易学,使易学向着哲学化倾向发展。最有名的便是《世说新语·文学》中载慧远与于易学深有造诣的殷仲堪“庐山论易”:“殷荆州曾问远公:‘《易》以何为体?’答曰:‘《易》以感为体。”[[vi]]当殷仲堪再问:“铜山西崩,灵钟东应,便是易耶?”慧远则笑而不答。这里,论易已不涉及易卜,而是何者为体的哲学问题。
佛教本是一种以求智慧、求真理的哲学,但人们常以易学中的神秘思想来表现佛教具有超越世俗的智慧,如易学中“感”的认识方法也不由自主地代替了佛教的理性认识方法。如竺道生认为佛与众生之间具有感应关系,佛无时不与众生感应,只是众人不能体觉。但佛教唯识宗认为当人们通过一套语言系统描述了一个世界之后,世界就成为了由该套语言的界限所界定了的世界,同时人们也就接受了这个语言系统所构造起来的世界。但由于人类的语言很不精确,利用语言对世界的言说,无论我们表述得如何,我们不能说世界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换句话说,人们利用语言对世界的言说将产生了“言不尽意”。受其影响,人们开始认识到周易中存在着精微之理,但卦象不能清楚地向人们显示了这些精微之理,系辞的所有表述都不能完整地表述出卦象之意。卦象就是摹仿事物的形状,立象的目的是为了尽意,而语言是对象的述说。但利用语言在对象进行言说的过程中,象能尽意,尽的是卦象之意,而非通于意外者也;系辞能尽言,尽的是系内之言,而非言乎系表者也;所谓意外者、系表者是非物象所能表示、非语言所能表达的。《周易略例·明象》:“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也就是说,他认为言不尽意。
再有,佛教哲学将语言当成为了一种文字游戏,是渡河之舟楫,指月之手指,它使我们在语言游戏中可洞察到佛法。如禅宗历史上的许多公案,问答双方,以看似无理可循的对话,而让对方悟到真理,便是利用语言的游戏作用。王弼可能深受佛教哲学中语言游戏说的影响,而提倡“得意忘言”,就是要求人们通过语言认识了卦象之意之后,便可以放弃对卦的所有言说,甚至卦象也应该放弃。即是把语言当作渡河之舟、或登高之梯,当在渡河之后,或登高之后,便应将舟船、梯子扔去。《周易略例·明象》:“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及“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重画以尽情,而画可忘也。”
在佛教的影响下,汉儒还对于易作出了抽象化的研究。如易就是变化,变化无处不在。《扬雄·太玄攡》:“(易)仰而视之,在乎上;俯而窥之,在乎下;企而望之,在乎前;弃而忘之,在乎后;欲违则不能,嘿则得其所者,玄也。”变化就是物本身发生变化,《列子·天瑞》注引:“吾之化,非物之所化,则化自化耳。化化者,岂有物哉?无物也,故不化焉。若使生物者也生,化物者也化,则与物俱化,亦奚异于物?明夫不生不化者,然后能为生化之本也。”其中,“吾之化,非物之所化,则化自化耳”指出了变化不是物的存在。“化化者,岂有物哉”指出了变化是一种现象,而不是一种物。“无物也,故不化焉”指出了如果没有物的存在,便不存在变化。换句话说,变化是物的变化。“若使生物者也生,化物者也化,则与物俱化,亦奚异于物”指出了如果万物的第一因(无物)可以继续向前追溯和“变化”本身也发生变化,那么,无物和变化便与物一样,成为了物的存在。郑玄还将变化分为三种情况:变易、简易、不易。“变易”是说,宇宙和人间的万事万物,没有一样是不变的。“简易”是说,尽管变很复杂,但任何复杂的现象都是由简单的现象复合而成,因此,我们可以把复杂现象还原为简单现象。“不易”是说,万事万物随时随地都在变,但惟有一样东西是不变的,就是这个能变万有的“变”,天地之间惟一不变的就是变化,它是永恒的。
二、隋唐时期
隋唐时,随着人们对佛教认识的深入,许多佛教派别以《易经》作为儒家的哲学著作,继续着佛教哲学与儒学的会通。如天台宗智凯引周弘正之说,判《易》、《老》、《庄》三家,以为“《易》判八卦,阴阳吉凶,此约有明玄;《老子》虚融,此约无明玄;《庄子》自然,约有无明玄”。[[vii]]华严宗李通玄以易解《华严经》,尤其是运用《艮》卦之义作解,对宋代学者影响很大。[[viii]]华严五祖又是禅宗荷泽四传弟子的圭峰禅师宗密,以乾德比佛德,以五常比五戒,试图借助群经之首的《周易》弘扬佛法。无住禅师释《易》,以为“易,不变不易,是众生本性;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是众生本性。若不变不易,不思不相,即是行仁义礼智信”。[[ix]]但与《易》关系最密切者,当数倾心于义理一派以华严宗的法藏和倾心于象数的是禅宗曹洞一系。
华严宗的法藏受到《易经》“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影响,以此解说法界缘起论,形成了一个不同于印度佛教的阿赖耶识学说,从而与法相宗认为真如是无为法的观点分庭抗礼。法藏认为:“谓真如有二义 ,一不变义,二随缘义。无明亦二义,一无体即空义,二有用成事义。此真妄中,各由初义故成上真如门也,各由后义成此生灭门也。”[[x]] 生灭门有两个组成部分,即随缘真如和成事无明。而随缘真如和成事无明又各有二义:一违自顺他义,二违他顺自义。于是生灭门下就建立起了一个类似于《易经》的“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的结构。然后又把这八义重新组合,即“八合四,四合二,二合一”,依次套迭入阿赖耶识(藏识)。
因为禅宗追求超越语言、逻辑、经典的束缚,而在前期易学中,曾模仿北辰居中,众星拱之之天象圆相,建立了一个以太极、太一为中,构想太一行九宫、太一配八卦的易学圆相图,作为认识世界的基本系统框架。易道圆相图恰合禅宗特殊的话语要求,从而被禅宗所吸收。禅宗既以圆相指代至上、完满之真如,又以圆相表征变化无尽之森罗万法。作为禅宗“五叶”之一的曹洞宗一系,从石头希迁至曹山,他们还从魏伯阳《参同契》入手,将汉代易学的象数模式引进佛教,并借鉴易学的阴阳交感之道,演绎出各种圆相图和卦图,以说明理与事、体与用之间的关系。希迁受到《周易参同契》重离、坎二卦的启示,将此二卦引入禅门,以离明坎暗说明明暗理事的关系。希迁的再传云岩昙晟则在坎、离二卦中独取离卦,以重离六爻中的相互融合来表达理事的变化。昙晟的弟子洞山良价依据“偏正回互”之意,建立“偏正五位”以说明禅修由浅人深的过程。良价还设立“功勋五位”,将修行过程分为向、奉、功、共功和功功五个阶次,说明洞宗的修行旨趣。曹山本寂禅师“借黑权正,假白示偏”,以黑白五种圆相图表征“五位君臣”。宗密以易理“太易→太极→两仪”的宇宙生成之道,比附佛教“阿赖耶识→一念业相→心境三分”的万法生成缘起之道。由于周易象数本身就非常隐奥,根据《周易》象数改造而成的佛教象数也就更显神秘莫测,曹洞宗的禅学思想也就越来越隐晦难解了。
三、宋代
因为宋以前的儒学在理论上侧重于政治伦理的说教,在综合说明宇宙和人生的理论方面是粗俗荒谬的天人感应观,其思辩性、逻辑性较差,在哲学本体论方面远比不上佛家。因此,宋儒深深地感觉到与佛教对抗的紧迫性,儒学复兴就成为了时代的要求。宋儒便用儒家和道家共同崇奉的《易经》作为反佛的理论武器——以易胜佛。其中,正统意识强烈的儒家学者一方面大量借用佛学理论以阐释易学,另一方面又极力批判佛学,企图以儒学削弱乃至取代佛学。而一些持包容开放态度的儒家学者则主张会通易、佛,这导致了儒学在哲学本体论方面吸收了佛道的合理内核,形成了从宇宙到人生的一整套系统为哲学理论,而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一一宋明理学,宋学也被称为“儒表佛里”。
在二程以前,宋代易学可以分为两派,即象数派和义理派。象数派以刘牧、周敦颐、邵雍等为代表,他们以道家的宇宙生成论为理论基础,以易学的象、数、图书为形式来说明世界。义理派则有范仲淹、胡瑷、欧阳修、李靓、王安石、张载等,他们继承王弼以义理解易的方法,但又与王弼以老庄解易不同,而是主宗儒学,阐述儒家义理。但无论是象数派还是义理派,均未解决将宇宙观和社会人生观相统一的问题。其中,象数派如周、邵等将偏重于宇宙观,且流于术数;义理派只是围绕着“太极是什么”来讨论,并根据各自的认识而相继引进了理、气、心等来解释太极,同时放弃了利用语言来言说易,实际上是将易学简单化和低俗化。至二程才将儒、释、道结合起来解易,以理作为世界与人生、宇宙观与伦理观相联系的枢纽,而建构了理学的基本框架。二程以后,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均从二程出发,形成了完整成熟的客观唯心主义理学和主观唯心主义心学的体系,在哲学意识形态中取代了佛教的统治地位。
整体而言,宋代佛教与易学的结合更多地在心性义理上。而佛学对易学影响最深的是《华严经》,其次是禅宗思想。《居士分灯录》称周敦颐自叹:“吾此妙心,实启迪于黄龙,发明于佛印。然易理廓达,自非东林开遮拂拭,无由表里洞然。”[[xi]]也就是说,周敦颐之学受到了临济宗黄龙派创始人黄龙慧南、佛印了元、东林常聪的影响。另,相传周敦颐曾向僧寿涯问学,僧寿涯以偈回答:“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能为万象主,不逐四时凋。”僧寿涯通过这四句偈告诉周敦颐在天地之先就存在着一无形的、寂静的永恒存在,它才是万物的第一因。在这一认识的影响下,周敦颐参照陈抟的《无极图》,将太极图加以改造,而写出了被后来理学家看作是为理学奠定世界观基础的开山之作《太极图说》。但周敦颐也明显受到华严宗的影响,《太极图说》中“无极之真,妙合而凝”此二句出自《华严经法界观》,“无极而太极”等语则是东林口诀。[[xii]]《通书·理性命章注》提出“万物之中各有一太极”也与华严宗理事观有关。但周敦颐又深受李通玄以艮卦解《华严经》的影响,认为:“佛氏一部《法华经》,只是儒家《周易》一个艮卦可了。”[14]因为,周敦颐以《华严经》专言止观,相当于《周易·艮卦》专言艮止之义。
邵雍继承了象数派的主张,但他也受到禅宗的影响,并将心性学说引进易学。他认为天地存在一个心,而心也是太极、道。《皇极经世·观物外篇》:“天地之心者,生万物之本也”及“心为太极,又曰道为太极。”受到佛教二分性哲学的影响,他将易学分为先天之学和后天之学。他认为伏羲八卦以乾、坤、坎、离为四正卦,是自然而生,囊括天地之文,万事之理,是先天图。因此,伏羲的八卦是先天学。而周易是对八卦的推演,进而又经过孔子的推演。因此,文王的周易是后天学。《皇极经世·观物外篇》:“尧之前,先天也;尧之后,后天也。”先天之学是心学。《皇极经世·观物外篇》:“先天之学,心法也。故图皆自中起。万化万事生于心也。”据此看来,他似乎把先天之学当作是追问万物本原的学问。而后天之学是由心所发之迹,心迹就是万物的运动变化之学。《皇极经世·观物外篇》:“先天之学,心也;后天之学,迹也。”据此,他似乎把物理学当作是后天之学。
张载痛陈自从佛教传入中国以来,对中国社会和民俗的危害,《正蒙·乾称篇》:“自其说炽传中国,儒者未容窥圣学门墙,已为引取,沦胥其间,指为大道。……故未识圣人心,已谓不必求其迹;未见君子志,已谓不必事其文。……自古诚、淫、邪、遁之词,翕然并兴,一出于佛氏之门者千五百年。”[[xiii]]在这段话中,张载指出了佛教的传播直接导致了儒家正道被弃置,儒者皆以佛教为精微高深之道,沦胥其间,而不求识圣人之心,不求闻君子之志;佛教对百姓的影响,在于它使得人伦不察、庶物不明、治忽德乱、无礼无学。实质上,儒家和佛教在“发本要归”处的殊归,佛教的发本要归处在“直语太虚,不以昼夜、阴阳累其心”,而吾儒则以易为要归处,由此断定儒是而佛非。《正蒙·乾称篇》:“彼语虽似是,观其发本要归,与吾儒二本殊归矣。道一而已,此是则彼非,此非则彼是,固不当同日而语。……大率知昼夜阴阳则能知性命,能知性命则能知圣人,知鬼神。……舍真际而谈鬼神,妄也。所谓实际,彼徒能语之而已,未始心解也。”[15]张载批评佛教只认识事物的本质属性,而不认识事物的运动变化,不能通晓《周易》,故并不能尽性。《横渠易说·系辞上》:“释氏之言性不识《易》,识《易》然后尽性。盖《易》则有无动静,可以兼而不偏举也。”[15] 在张载看来,道、神、易其实是一体的不同称为谓,它推行于虚实之间,称其为道;虚实间感应变化不测,称其为神;虚实间生生不已变化周流,称其为易:“体不偏滞,乃可谓无方无体。偏滞于昼夜阴阳者物也,若道则兼体而无累也。以其兼体,故曰‘一阴一阳’,又曰‘阴阳不测’,又曰‘一阖一辟’,又曰‘通乎昼夜’。语其推行故曰道,语其不测故曰神,语其生生故曰易,其实一物,指事而异名尔。”[15]。
但张载也受到佛教的影响,如张载批评佛教以虚为本体,而不通昼夜、阴阳之道。而阴阳有无虚实本通为一物,佛教拆分了这一组相对的象,将其中虚无的一方绝对化,当作世界的本根:“有无虚实通为一物者,性也;不能为一,非尽性也。饮食男女皆性也,是乌可灭。然则有无皆生也,是岂无对?庄、老、浮屠为此说久矣,果畅真理乎?”[15]因此,佛教必然以现象世界——即有形之气形成的世界为幻化:“若谓万象为太虚中所见之物,则物与虚不相资,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于浮屠以山河大地为见病之说。……明有不尽,则诬世界乾坤为幻化。”[15]但张载又认为万物是神化所致,万物是神化的糟粕。《正蒙·太和》:“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及“万物形色,神之糟粕。”糟粕应不是真正的存在。
程氏继承了周敦颐的认识:“周茂叔谓一部《法华经》,只消一个艮卦可了”;又说:“看一部《华严经》,不如看一艮卦 (经只言一止观)”;“艮卦只明使万物各有止,止分便定。”[[xiv]]但二程并不满足于此,他们返回儒家立场,借用佛教之理,进而批判佛教。程颢说:“艮其止,止其所也。各止其所,父子止于恩,君臣止于义之谓。艮其背,止于所不见也。”[16]这就是说,儒家之艮止与佛教之说不同,当止于儒家义理、纲常伦理之上,而非止观之义。他又说:“艮其止,止其所也。八元有善而举之,四凶有罪而诛之,各止其所也。释氏只曰止,安知止乎?”[16]这是说佛教以止言止,不知所止,不知为善止恶,便不知动与止的辩证关系。程颐对艮止之义也有阐释。他在《易传》中明确地指出:“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动于欲也。……止于所不见,则无欲以乱其心,而止乃安。不获其身,不见其身也,谓忘我也,无我则止矣。”[16]由此可见,程颢改造佛教止于性空为止于理,程颐则进一步借助佛教无欲、忘我之念,来阐释儒家的去人欲、存天理的思想。但二程也承认佛“亦尽极乎高深”,“ 佛老,其言近理”;“佛亦是西方贤者”;“安可慢也”。程颐的《易传序》“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出自唐清凉国师《华严经疏》。《华严经》的真空绝相观、事理无碍观、事事无碍观,如镜灯之类,包含万象,无有穷尽等语,程颐将之归纳为“万理归于一理”。[16]二程吸收了华严宗的“真空绝相观”,“事理无碍观”,“事事无碍观”,“一言以蔽之,不过曰万理归为一理也”等,程氏还将佛禅之悟与孟子之觉”相等同。二程的心性修养之说,也多与佛禅相通。所以,朱熹在《朱子语录》中说:“伊川偷佛说为己使。”
二程提倡以儒家义理解易,二程理学的许多重要概念和观点便是在解易中提出来的。如伊川在回张闳中的信里说:“谓义起于数则非也。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欲穷象之隐微,尽数之毫忽,乃寻流逐末,术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务也。”二程还说易不可逐句看,要以己意解易,重在阐明儒家义理。
南宋时,理学中各派对于《太极图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并出现了不同的认识。其中影响最大的便是朱熹和陆九渊进行了一场“无极太极之辨”。在这场争论中,朱子认为《太极图说》提出了无极,是将太极中的“无”之义界定出来,使“太极”的内涵得到清楚的界定。朱熹认为如果不设立无极,则因为太极是一物,那么,太极便不能作为万物的本原。如果不设立太极,则因为无极是无,那么,又不能解释万物是如何从无到有的。《太极图说解》:“不言无极,则太极同于一物,而不足为万化之根;不言太极,则无极沦于空寂,而不能为万物之根。”正因为设立了太极是从无极下降而来的最高最大实体,由太极承接从“无(无极)”到“有(万物)”的作用,从无到万物之间就不缺少了一个中间环节。《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圣人谓之太极者,所以指夫天地万物之根也。”据此,朱子把《太极图说》的首句“自无极而为太极”改为“无极而太极”,即认为太极和无极是同一个“东西”的一体两面。基于这一认识,朱子很少使用无极这一概念,而多以太极来表述无极的“无”。同时,朱熹还特别强调太极不是一物,而是“无”形之极。《周子全书·太极图说·集说》:“周子所谓无极而太极,非谓太极之上,别有无极也,但言太极非有物耳。”
与朱熹的认识不同,陆九渊认为前人未曾论及无极,“无极而太极”似表示了无极在太极之先,不符合儒家“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说法。由此他否定了无极的存在,而以太极作为万物最终极原因,并认为太极不是物的存在。《陆象山全集·答朱元晦》:“夫太极者,实有是理”及“易大传曰:易有太极,圣人言有,今乃言无,何也?作大传时,不言无极,太极何尝同于一物,而不足为万化根本耶?”
针对陆九渊的这一认识,朱熹明确指出对于周易的研究不应拘泥于前人之说。《朱文公文集·答陆子静》:“伏羲作易,自一画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尝言太极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赞易,自太极以下,未尝言无极也,而周子言之。夫先圣后圣,岂不同条而共贯哉!”从上可见,正确的一方应该是朱熹。
四、明清时期
明代,在佛易关系上,僧人们把易当成佛教经典来解读,于是以佛解《易》成为明代易学的一大特色。比如,李贽[[xv]]在《续藏书》中就记载了明代一个名叫雪庵的和尚率徒众将《易经》当成佛经来诵念。
明末高僧紫柏真可将《易经》当成了佛教的《金刚经》,都是在阐述既无心又有心的空。他从《易·系辞上》:“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睛状。”由此得知《易》从三个方面讲天地之道:幽明之道,死生之道,鬼神之道,而这三大天地之道即是大觉之教,也就是释伽牟尼的教导。首先,就生死之道而言,真可引龙树的《生死偈》为证,阐明身之死与生之间“犹若环轮,孰为始终”,此契于《易》之“原始反终”义。其次,就幽明之道而言,真可依据佛教唯识学“心识变现万法”的原理,认为幽明“本乎有心”,世界皆由心识之所变现,未变现为幽,已变现为明。最后,就鬼神之道而言,真可认为鬼神亦“本乎有心”。鬼神的实质是魂魄,而人的魂魄则是缘人的性情而有。因为性和情乃是心的两个方面,故魂魄缘性情而有即是缘心而有。很显然,真可在这里是从“万法唯心”的佛理出发,认为物质世界和鬼神世界皆从心生,并非实有,从而将《易经》所讲的三大天地之道”诠释成了佛教的大觉之教。
印度佛教以意和识论心,而中国佛教在受儒家心性论影响后则往往以情和性来论心。如 何构建并阐释情、性、心三者之间关系,就成了中国佛教心性论的核心内容。真可在《解易》一文中认为,《易经》的卦爻中蕴含着中国佛教心性论所要言说的情、性、心三者之间的关系。《易经》的六十四卦作为一个整体乃是心之本体,而其中的每一卦则是心的具体相状,包括情和性两个方面。组成卦的六爻因为变动不居、忽吉忽凶而代表变化无常之情;由六爻所组成的卦,不管六爻如何变动不居,其作为一个整体的相状 (即卦象和卦义)都是稳定不变的,此代表本自不动的性。这即“卦寓性,爻寓情”。而心乃寓乎卦爻之间,可以统情性,一微涉动则爻显情生;一心不生则卦显性现。《易经》所讲的卦爻变化,实就是佛教所讲的无常之道。因为,卦寓性,爻寓情,所以,卦爻无常表明性情也无常。情无常而可即情而复性,性无常而可即性而摄情,这就化解了情和性之间的矛盾。
佛教讲信顺。也就是信受所闻之佛法而随顺之,不执著。大凡佛经,皆以“如是我闻”开头,智凯认为“如是”两字乃是表示佛教信顺的标志性话语。真可认为,在《易经》的六十四卦中,“大有”卦蕴含着佛教信顺之义,一个学佛者若能具备“信顺尚贤”之三德,那么诸佛法便都能为其所用,令其身心受益而大有。大有卦一阴五阳,一阴(六五)比喻学佛之众生或佛教徒,五阳比喻五乘诸佛法。一阴居尊而五阳归之,一阴统领五阳,是为大有。在学佛者应是阴柔而居尊的,就像大有卦之六五,因为唯有阴柔,学佛者才能信顺佛法崇尚佛;唯有居尊,学佛者才能成为佛法的主人而不至于在学佛过程中丧失自己,成为佛之奴仆。佛教主张破烦恼而达于无我的空境,真可认为这正是《易经·噬嗑》的寓意所在。因为该卦上是离,而离为火,火不至空亦不止也。空是火之极,火至空象征着佛教修行至于无我之空的最高境界。在噬嗑卦的六爻中,真可以初九噬乘己之六二、六三噬乘己之九四和处尊的六五来象征佛教修行中的破烦恼 (噬嗑即是咬破的意),以上九象征破了烦恼而达于无我之境,进入能容天地万物之空境。上九之爻辞“荷校灭耳”即比喻一切烦恼都灭尽了,人生毫无负累。
真可结合《华严经·人法界品》中善财童子往南方参学求法的故事分析了离卦的佛学意蕴。在真可看来,善财童子之所以舍东、西、北三方而独往南方参学求法,并不是因为他偶然的心血来潮或一时念起,而是因为南方是离卦之所在。从卦象上看,离卦之中间一爻为阴爻,呈中虚之象,中虚象征着自心之虚灵而明。离卦蕴含心义,但离卦之心指某一具体个体的心,即所谓的自心。善财童子向南方参学求法,实寓向自心求法之意;而向自心而不向外境求法,这正是追求明心见性的禅宗所要求的。
另一位明末高僧蒲益智旭,目睹除净土宗之外,佛教各派都已经衰落。尤其是禅宗,“以心传心,不立文字”的传统规则恶性膨胀,既不习经也不坐禅,其棒喝机锋在数百年的流传中,也早已失去其本来意义,成为不学无术者遮掩其窳陋的把戏,为有识者所深恶痛绝。对于这一点,云栖株宏曾讽刺道:“ 古人棒喝,适逗人机。一棒一喝,更令人悟。非若今人,以打人为事。”智旭每每中夜痛哭流涕,以致尽情痛骂:“法师是乌龟,善知识是忘八。”智旭便扮演起“救禅大夫”的角色,他所开出的“救禅处方”有两个方面,一是在佛教内部融会诸宗,强调性与相、禅与教以及禅与净的融会贯通;二是在佛教外部,主张儒佛一家,三教同源。主张援佛入儒,以佛释儒。在他的著作集《灵峰宗论》里,以佛释儒的例子比比皆是。表面上看来,智旭是在以佛释《易》,实际上他则是在“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企图借《周易》之“躯”还禅宗之“魂”。
智旭将《周易》视为儒家的本源之作,认为儒家后来的一切思想包括四书中的思想都是从《周易》中衍化出来的。智旭解《易》,既以《易》理启悟慧观,又以《易》理诱导修行,将佛法、修行与《易》理相结合。在《周易禅解》中,既可以看到佛学概念与易学概念之间的对释,也可以看到佛学思想与易学思想之间的互释。智旭认为:“易即真如之性,具有随缘不变、不变随缘之义,密说为易。”[[xvi]]智旭在解释《周易》的卦和爻时则用天台宗的“法界互具”来解释卦和爻。易若以思想来说,是儒家之易;以术数论之,系筮家之易;以因缘解之,系释氏之易。玄妙易理,不离佛性。智旭以《周易》的乾元喻佛性,以示佛性无所不在 (《周易禅解·乾·彖》)。而乾刚坤柔,止观定慧。乾健坤顺,阳刚阴柔,是《周易》概括宇宙万有生成变化的基本范畴。《周易禅解·系辞上》:“盖易即吾人不思议之心体。乾即照,坤即寂。乾即慧,坤即定。乾即观,坤即止。若非止观定慧,不见心体。”[[xvii]]智旭还以三止三观诠释乾父坤母及六子,认为惟有止观双运,乃得解脱。《周易禅解·睽》:“惟根本正慧,能达以同而异,故即异而恒同。否则必待定慧相资,止观双运,乃能舍异生性入同生性耳。”[19]四悉檀为梵语,有教化之义,指普施教法,令众生受感化而有成就。智旭以伏羲阴阳之象解读世界悉檀,为随顺世间之法,即以世间共通的观念与语言来说明缘起的道理。《周易禅解·上经之一》:“伏羲但有画而无辞,设阴阳之象,随人作何等解,世界悉檀也。”智旭以文王彖辞之义解读为人悉檀,系应众生各别的根机,说各种出世实践法,使众生生起善根。《周易禅解·上经之一》:“文王彖辞,吉多而凶少,举大纲以生善,为人悉檀也。”智旭以周公爻辞之理解读对治悉檀,是针对众生贪、嗔、痴等,应病与药一一加以对治,使众生断除诸恶。《周易禅解·上经之一》:“周公爻辞, 诫多而吉少,尽变态以劝惩,对治悉檀也。”智旭以孔子十传之学解读第一义悉檀,即破除一切语言,直接以第一义诠明诸法实相之理,使众生真正契入教法。《周易禅解·上经之一》:“孔子十传,会归内圣外王之学,第一义悉檀也。”佛教要求不执着于“四句”中的任一句,也就是所谓的“不堕四句”,堕在任一句都远离了佛教的旨意。智旭认为他的解易是一种“不堕四句”式的佛行。智旭所说的易、非易、亦易亦非易、非易非非易明显模仿佛教的“四句”。
明末清初,曹洞宗殿军人物永嘉元贤禅师为石头希迁《参同契》作注,注重由于离卦而来的既济、未济、益、损四卦,与离卦一道配以正中偏、偏中正、兼中至、兼中到、正中来,形成新的“五位君臣图”。五位总图融合了圭峰宗密的阿赖耶识圆相图与曹洞宗的五位君臣图,说明体用、理事之间一体又交互的关系。永嘉元贤批判了周敦颐《太极图说》的动静之说。他认为周敦颐的太极等同于道体,道体不能以动静言之。“曰不动不静者,太极之体。有动有静者,太极之用。”太极之体不动不静,太极之用才有动有静。周敦颐“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混淆了体与用之间的关系。

五、近现代
近现代,随着佛教复兴唯识学的思潮,也出现了以唯识论易,并融入了西学思想,倡导易的世间法与出世间法,使佛学易向现代化转型的新局面。太虚大师在《佛学源流及其新运动》中认为佛教的改革应“于现代交通的互助的人类底共存共荣关系上,东西各民族的人生哲学基础上,以大乘初步的十善行佛学,先完成人生应有的善行。开展为有组织有纪律的大乘社会生活。一言以蔽之,佛教要想有所发展,就必须立足于现世和人生。至此,拉开了持续自今的“人间佛教”运动的序幕。
太虚大师把《易传》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再依八卦而生六十四卦的易理与“唯识缘起世界众生”的佛法相比拟,推导出一套新的佛教易学体系。在《易理与佛法》中认为:“易经所讲的为世间根本法与枝末法,与佛法上所说的唯识缘起与因果流转相近。”在太虚看来,“本识”是世间法的根本,世间一切根身、器界皆为本识所变起。《论周易》:“本识本无自性,不守其性,奄然不觉,谓之无始无明住地,则即一画之太极也。”[[xviii]]本识本是无始无终、无边无中、无内无外的。这相当于易学符号系统中的最初一画。由于本识不守其性,不觉而动,即形成不生灭与生灭和合的阿赖耶识,以及执着阿赖耶识中真如为我的末那识。能执的末那识与所执的第八识之我,可比易学中的阴、阳两仪。第七、第八能执、所执相应的“无始四惑”即我痴、我见、我爱、我慢,相当于易学的少阴、太阳、少阳、太阴四象。在此基础上,展转相依相缘,各由根、尘、识三和合而成八识:乾比第八识、坤比第七识、依乾坤之七八两识别,演变成第六意识及眼、耳、鼻、舌、身前五识,可比艮、震、坎、离、巽、兑六卦。由八卦变为六十四卦,可比由八识三能变以成世间万物。
而修学大乘佛法,须经过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佛等阶段。这些阶段一一可用乾卦的爻位来解释。在《论周易》中,太虚大师将《周易·乾卦》的爻位与佛教修行的次第相比较,认为初地为初九“潜龙”,二二地为九:“田龙”,四五地为九三“君子”。七地为九四“渊龙”,八九地为九五“飞龙”,佛地土为上九“亢龙”,佛身土为用九“群龙”。佛地虽“种习俱尽,异熟全空”,却因住涅而有悔;只有当“全法界为一佛身土”时,才是圆满之义。
而现代新儒家则坚守着以易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阵营。如马一浮[[xix]]继承了二程“看一部《华严经》,不如看一艮卦”之说,认为艮卦辞“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即是佛教所言的无人相,无我相,是破除人我二执后进入“无相三昧”境界之显现。佛理言艮即为寂灭义、不迁义、自性清净义。艮止即狂心顿歇。歇即菩提。心止则妄息,息妄为真。故止是寂灭义。艮止其所,上下敌应不相与即为一切处不迁义。概言之,艮止中蕴含了破除人我二执的工夫、顿歇狂心的法门、显现清净自性的要义等等诸多的佛理义趣。而华严宗的终顿圆三教并用,在易教则为乾坤并列,而易道见乎其中。其本质都是彰显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之理。
关于郑玄认为易有三义:变易、不易、简易,马一浮结合《华严法界观门》中的真空观、理事无碍观、周遍含容观,提出真空观相当于不易义,理事无碍观相当于变易义,周遍含容观相当于简易义。三观皆在法界,三义统摄于易,易教即可以被理解为一真法界。《大乘起信论》以随缘不变释不生不灭义,以不变随缘释生灭义。其所说的生灭义,即是易道的变易之理。不生不灭之真相,即是不易义,而不变随缘,随缘不变,则可与简易之理相参。中观派以缘起性空,双离断常,以中道立论。马一浮认为“只明变易,易堕断见。只明不易,易堕常见。须知,变易元是不易,不易即在变易。双离断常二见,名为正见,此即简易也。”在《三易略义》中,他认为不易是指体大,成就涅粲德,显法身;在儒家言是指天命之谓性,它不生不灭,是指位而言,以诚而通之。变易是指相大,成就解脱德,显应身;在儒家言是修道之谓教,生灭之所,是气之聚散,万物资始,乾道变化。简易是指用而言,成就般若德,显报身;在儒家言是指率性之谓道,不变随缘,随缘不变,指德而言,是诚之源。
马一浮还认为,易教与佛理可以互证相参,从根源上讲即缘于人之本心。从心学的角度言,易道只是本心的外显,故而可以假易道以体悟本心本体。而爻者,效也,但所效不仅是外在的成象,更主要的是效心之所动。因而卦爻所显皆是心之动念所在。那么易教所揭示之理即不在于外,而应收归于本心。易教之洁静精微,佛法亦在其中。洁是指不受杂染诸惑,即是无垢义。静是指常住正念,无诸般攀缘杂虑,即不迁义。精指能够参透一切法相,即真实义。微则指见诸相非相,即深密义。只有透彻见悟了这四点才能算是有得于易教。
[i]夏金华著:《佛学与易学》[M],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版。
[ii]王仲尧著:《易学与佛教》[M],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
[iii]谢金良著:《(周易禅解)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版。
[iv]释僧祜著:《出三藏记集》卷十三《康僧会传第四》[M],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P514。
[v][梁]慧皎著,汤用彤校注,汤一介整理:《高僧传》[M],北京:巾华书局,1992年版。
[vi]刘义庆著,曹瑛、会川注释:《世说新语》[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vii]智凯:《摩诃止观》卷上[M],台南:湛然寺,1995年版,P981;卷三下,P240-241;卷六,P569。
[viii]邱高兴:以(易)解《华严经》——李通玄对《华严经》的新诠释。周易研究,2000(1):P59-65。
[ix]佚名:《历代法宝记》卷下[M],见蓝吉富主编《禅宗全书》第l册,台北:文殊出版社,1988年版,P139。
[x][美]华伦莱著:《<易经>与华严宗学说的形成》[A],见黄寿棋,张昔文主编:《周易研究论文集》(第4辑 )[C]。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xi]朱时恩著:《居士分灯录》卷下《周敦颐》[A],蓝吉富主编《禅宗全书》第14册[C],台北:文殊出版社,1988年版,P1328。
[xii]宗本著:《归元直指集》卷下《儒宗参究禅宗》[A],见藏经书院《续藏经》第108册[C],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
[xiii][宋]张载著:《张载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
[xiv] [宋]程颢、程颐著:《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
[xv]《李贽文集》第4卷《续藏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P144。
[xvi]释智旭著,曹越主编、孔宏点校:《明清四大高僧文集·灵峰宗论·答问·性学开蒙答问》[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P197。
[xvii]释智旭著:《周易禅解》[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年版。
[xviii]太虚著:《太虚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xix]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马一浮卷》[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来源:“此是读哲学”公众号
欢迎关注@文以传道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