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留学时的季羡林
为方便后文的叙述,先要明确两则概念。
其一,关于印度学。所谓“印度学”,译自德语Indologie(英语Indology)。在欧洲,至少在季羡林先生留学德国的时代,“印度学”主要以梵文、巴利文等古代语言文献为研究的对象,并基于这些语言的文献,而展开对印度古代文化、宗教等领域的研究。季先生留学的时代毕竟已成往昔,时代演变至今,德国的学科建制也经历了调整,但是迄今为止,尤其是在德国,如果一家研究所或者大学专业的冠名之中含有Indologie的字样,说明这里还在教授梵文等印度古代语言,还在以印度古代的语言、宗教、文学等为主要研究科目。当代德国,在延续印度学传统的基础上,更增强了对现代南亚次大陆各国各领域的研究。为了与过去的传统学科加以区别,将南亚次大陆各国的语言、文化设为主要专业科目的大学,多采用“南亚研究”为名称。例如海德堡大学设有南亚研究所,下设古典印度学和现代印度学。这样的冠名体现了学科的调整,也折射出这背后的思索:传统意义上的“印度学”,已经不能涵盖当今学科的发展。因此,在实行对学科建制进行调整的同时,也要对学科的名称进行调整。鉴于“印度学”之概念的由来,本文所用“印度学”之概念,仅限于古典范畴。
佉卢文函牍
其二,关于philology一词的翻译,需要加以说明。这个词汇,有学者主张译作“语文学”,其中的“文”或可指文献,或可指文字。这样一来,“语文”似乎是个缩略语,可以是“语言文字”的缩略,也可以是“语言文献”的缩略。也有学者把这个词译作“历史语言学”,把欧洲古典学派的general grammar之概念译作“普遍唯理语法”。然而,无论语文学,还是“历史语言学”,均与法国哲学家福柯(Foucault)所阐释philology有一定的距离。依据福柯的分析,19世纪之初诞生的philology,第一次将语言作为语音元素的整体来对待。“语言的整体存在是音的整体存在。”(Michel Foucault, The Order of Things——an Archae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 New York, 1973, p. 286.以下简称:Foucault 1973) philology实际上尤其提升了人们对语音元素的认知:说出的话,才是语言最真实的存在。对于语言的新认知,甚至影响到德国浪漫派对口头文学的注重。鉴于philology对语音的认知,笔者既不大赞同把这个词汇译作“语文学”,也不大赞同把这个词汇译作“历史语言学”。诚然,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学者,多运用比较的方法,好以古老的语言为对比的基础,以探寻某种语言的内部结构。但是,这样的探寻并不局限在历史的范围内,例如这一学派的创始人之一Jacob Grimm所著《德语语法》,即是对现代语言的关注。鉴于philology的内涵,为避免造就过多概念而产生的混乱,笔者回归简单。这里仅需说明,凡本文中所用“语言学”,全部缘对philology一词。
季羡林手稿(局部)
1935年底,正值24岁盛年的季羡林来到德国哥廷根大学。他最终选择梵文、巴利文等所谓印度学(Indologie)为主修专业,因为他认为:
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发明。在德国能把想学的几种文字学好,也就不虚此行了。(季羡林:《季羡林自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版,第76页)
那么为什么一定要在德国学习这些语言文字,学习梵文呢?这是因为:
尤其是Sanskrit,回国后再想学,不但没有那样的机会,也没有那样的人。(《季羡林自传》,第72页)
季羡林:《季羡林自传》
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
从这一思择的过程可读出如下实事:一者,当年中国社会没有印度学。二者,德国有。三者,这门学科能够成就日后在中国的发展,因为中国文化曾受到印度文化很大影响。
印度与德国不是近邻,相距遥远,历史上也不曾受到印度文化的巨大影响。那么,没有受到印度文化影响的德国缘何在大学的科目中会设有印度学呢?为探索此问题,笔者选择跟随福柯(Foucault)的理论而回顾19世纪初期,这是印度学在德国的初创期。
依据福柯的理论,在十九世纪的欧洲,三大学科从古典的模式脱颖而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崛起于古典学术之侧。这三者是:基于达尔文的进化论而产生的生物学,政治经济学,以及语言学(philology)[1]。这三大学科的诞生,标识欧洲的学术告别了古典时期,意味着现代学术划时代的开端。三大学科的并出,有其必然联系。而依笔者之见,这三大学科之中的语言学获益于欧洲学者对梵语的认知,它的诞生同时伴随着印度学在欧洲的形成。甚至可以说,是欧洲学者对梵语的认知催生了语言学。在福柯的笔下,19世纪语言学的形成主要以几个关键性的人物和他们的作品为基础。他们是Schlegel以及他的关于印度语言和哲学的论著,Jacob Grimm和他所完成的德语语法,以及Bopp和他所写作的梵语变位体系。这三个人物,实际上体现了发展过程的两个阶段,一是德国学术界对印度语言文化的接受,二是受到影响后基于本土文化所完成的开创工作。
暂且离开福柯的理论,先对他笔下的标识性人物多少做些绍介。Friedrich Schlegel,《论印度人语言和智能》(德语书名:Ueber die Sprache und Weisheit der Indier)的作者。这部的著作出版在德国曾引起轰动的效应。而实际上,对于德国印度学的发展起到奠基并推动作用的,是Schlegel两个兄弟。兄弟二人同时是德国文学史上浪漫主义的发起人和领袖。与德国文学史上那些著名的文豪诸如歌德、席勒一样,这兄弟二人最初也是凭借英译本而阅读了印度古典诗人迦梨陀娑的剧本《沙恭达罗》,并由此产生了对印度古典文学的浓厚兴趣。换句话说,是来自古代印度的《沙恭达罗》唤起了德国知识阶层对印度梵语文学的兴趣,这是导致印度学成为德国大学专业科目的原因之一。
Ueber die Sprache und Weisheit der Indier
《论印度人语言和智能》
Friedrich von Schlege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
当年F. Schlegel 在他论著的导言中写下这样一段话:
惟愿印度学能知遇那样的开拓者和倡导人,犹如15世纪的意大利和16世纪的德国因为一些人对希腊的研究而见证了伟人的突然兴起并在短时间内取得了伟大业绩。此时期,对古典认知的再度发现,迅速改变了科学的构架,甚至可以说是世界的构架,并使之焕发了朝气。我们大胆地预言:若是着力推动并引入到欧洲的认知范围内之后,当前印度学带来的影响,将同样伟大和广泛。(笔者译。原文转见于Heidrun Brückner, Klaus Butzenberger etc.编:Indienforschung im Zeitenwandel, Analysen und Dokumente zur Indologie und Religionswissenschaft in Tübingen, Tübingen, 2003, p. 5. 以下简称Indienforschung。)
Schlegel的这部作品的划时代的意义在于:它标识德国知识界已经从对印度古典文学的接受,过渡到对印度古典文献的语言研究。它奠定了德国梵文研究的基础,德国印度学的基础。Schlegel的著作把“有机体系”这一概念引入到了语言理论之中。一个新的学科,即比较语言学,已然呼之欲出。
上述《论印度人语言和智能》的作者,是Schlegel两兄弟之年轻者。他的哥哥,August von Schlegel本以翻译莎士比亚的著作而享誉德国,开始学习梵语的时间要晚于他的弟弟。但是, A. Schlegel支持梵语语言学的研究方向,他本人以48岁的年龄才开始在巴黎学习梵语,与他同学者还有日后成为比较语言学创始人的Franz Bopp。1818年,A. Schlegel 因德高望重而获得了德国波恩大学第一任印度学教授的教席。这是划时代的一年,以此为标识,印度学正式步入德国学术的最高殿堂。
Franz Bopp
[德]弗朗兹·葆朴(1791-1867)
福柯笔下同为19世纪语言学的奠基人中,Bopp是较为中国学界所熟悉的。1816年,他发表了《论梵语动词的变位体系及与希腊、拉丁、波斯及日耳曼语的联系》之论文,发表了直接从梵语译出《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故事选和吠陀诗选,由此而一举成名,成为比较语言学的创立者。那一年,Bopp 25岁。随后,Bopp居住伦敦,校订梵语《摩诃婆罗多》之故事《那罗传》,并把他原用德语撰写的论文翻译成英语。在伦敦,他知遇柏林洪堡大学的创建者,普鲁士贵族Wilhelm von Humboldt,并曾经教授后者梵语。1825年,Bopp成为柏林大学的东方语言的全职教授。至此,德国已经拥有波恩和柏林两个中心,开设出培养梵语和印度学研究的课程。从那时起,德国的印度学开始了它的蓬勃发展,研究的中心从古典梵语,到吠陀,成果层出不穷。
《摩诃婆罗多》插图
19世纪初期欧洲新兴的语言学处处烙印有印度传统的影响。印度古代对语言的观察和认知把欧洲人对语言的认识带入了新的视野。简而述之,依印度传统,梵语是一独立的体系,好比一张无破绽的网,构成这一系统的语言的各个成分,按照一定的规则排列组合,犹如是织成网的经线。梵语以名词性词和动词的变化为主要线索,表述行为、状态、意愿、致使的词根,构成语法结构的核心。所谓名词性词和动词之间,唯有形态的不同。一定的词缀附着在动词词根后,引起音变,可以变化成名词,或形容词,或分词。但作为名词性词的动词依然可以保持动词的特征,例如主动性,或者被动性。统而言之,梵语的词缀分为六大类,名词性格尾词缀,即义净所言“苏盘多”。动词语尾词缀,表示人称变化的语尾独立构成一类,即义净所谓“丁岸哆”,依“二九之韵”而演化。另有阴性词缀类,动词词根词缀类,原始词缀类,以及派生词缀类。梵语名词有著名的所谓八格屈折形态,而促使名词屈折变化的,其实只是七格三数的格尾,俗称呼格是第一格的衍生形式。古代印度人认为,梵语的格尾是含有指示意义的语言成分。当动词表述行为,构成语句,名词所指代者因直接参与行为而加入句中。此时格尾的功能,在于指示出此名词在行为中充当的角色,是行为的施动者、客体,工具、所从发生,以及行为的发生处。俗称第六格尾可以不参与行为,而主要表达二者之间的关系。印度传统除了擅长对语言组成结构进行剖析,尤其注重观察语音的变化,例如i e ai与y之间的升级、互动,等等。
《罗摩衍那》写本
印度传统对语言的认识,为欧洲的语言学家开拓了新的眼界。原来语言除了有所指示的客体的词汇,还有一些功能性的成分,原来构成动词变位的那些语尾、加在名词后的格尾,是独立存在的,这些指示语法功能性的成分具有意义。正是这些功能性的成分,构建起语言的内部结果。对语言的崭新的认识,使19世纪初期的欧洲语言学家把眼界从旧有的对修辞色彩、论证风格的评判,转移到对语言内部结构的关注。在古典时代,欧洲对语言研究,局限在对语言表达习惯的研究。这样以修辞、表述习惯、辩论风格作为分类的基础,语言便有了高低贵贱之分,划分出所谓“情感的语言”、“奴隶的语言”,或者所谓“文明的语言”、“野蛮人的语言”等等(Foucault 1973, p. 282, 285.)。受到印度传统对语言认知的启发,19世纪初期的语言家终于发现,任何语言都有独特的内在结构。这种内在结构,才是语言的根本特征所在,不受论说者所阐述内容的辖制。相反,任何论说者必须遵守语言的内在结构,受到语法规则的严格制约。一种语言与另一种语言的差别仅仅是二者自主的内在结构的不同。语言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不存在所谓“文明程度低劣”的语言。以语言的内在结构作为判断特性的标准,以语言的语法构成作为衡量的标准,于是各种语言处完全平等的水平之上,这才真正获得了各种语言之间比较的基础,例如梵语、拉丁、古希腊语在语法结构上有大量可比之处。而考察语言之间近似的语法结构,则揭示了语言之间继承和派生的亲缘关系,由此而可划分出所谓印欧语系,闪米特语系等。
印度传统对语言的分析,认为动词是话语的核心。这就意味着,语言的常量存在于表达行为、状态、愿望以及致使等动词的词根之中,意味着“语言并非植根在可以感知的客体中,而是植根于灵动的主体中”(Foucault 1973, p. 290.),活生生地存在于人民之中。民间有最生动的语言,这样的理念,引导着德国文学的浪漫派把眼光投向民间。当这样的理念孕育成熟时,也就不难理解,缘何德国的格林长兄的纯语言学模式的德语语法以及格林两兄弟参加编纂的词典诞生在19世纪初期。正是在这一时代,流传在民间口头的“格林童话”终于形有了文字版本,从此走遍天下。如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有天的地方,就有白雪公主的故事流传。而在造就了这些文化成就的背景之处,有印度学以及语言学在欧洲的新兴。
《格林童话》插图
[德] Paul Friedrich Meyerheim 绘
回顾印度学在德国的诞生之初,似可以得到这样概括性的结论:梵语文学、印度传统对语言的认识奠定了德国印度学的基础,与欧洲19世纪初期形成的语言学结伴而生的,还有印度学。而印度学的引入确实如Schlegel 所预言的那样,对德国乃至欧洲的学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改变了欧洲学术的框架。后来,曾跟随Bopp学习梵语的Max Müller 进而把印度学从比较语言、文学领域带入比较宗教学视野。关于印度学在欧洲的不可或缺他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如果我们把视野仅仅局限在希腊罗马的历史,局限在撒克逊人、凯尔特人的历史,捎带上些巴勒斯坦、埃及、巴比伦的背景色彩,而将我们最近的智慧亲属排斥在视野之外,……那么我们对整体历史的知识,对人类智能发展的洞察,就将是非常不完善的。”(Friedrich M. Müller, India – What can it teach us? was first published in 1883, reprinted in New York, 2007, p. 11,以下简称Max Müller reprinted 2007)印度学研究者的成果,还在19世纪时甚至已经进入小学生的课本,即德语、英语、法语等,都是印欧语系的一支。欧洲人终于发现,他们眼中曾经被视为野蛮民族的印度人,其实是亲戚[2]。
19世纪初期创立的欧洲语言学之浪潮,甚至波及到中国。曾经留学法国的马建忠于19世纪末创作了《马氏文通》,“引进西方的语言学深入研究了汉语的语法,构建了我国第一个完整的汉语语法体系”(宋绍年,《〈马氏文通〉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2页)。
马建忠《马氏文通》
商务印书馆,1904年
以上概述印度学在德国之兴,欧洲19世纪语言学之兴,以及语言学依福柯的理论在欧洲学术史上的意义,主旨在于揭示:印度学,这看似边缘的学科,曾经在欧洲引起伟大而深刻的影响。这门学科看似边缘,实际不边缘。当季羡林来到德国时,印度学已经过蓬勃的发展,经过沉淀,而成为德国的著名学科之一。如果不做这样的介绍,不做关于印度学在欧洲发展的背景的介绍,今日华语读者恐难理解季先生当年在哥廷根为何选择了那样的题目,即以混合梵语的《大事》诗文部分动词变化作为考察的中心,来完成自己最初的著述。季先生当年选择的这个题目,选择对语言的结构进行分析考察,显然是对在德国土壤上成熟发达的语言学传统的缵续。而另一方面,这篇论文其实已经体现了开创性的一面。
印度学,自1818初始在波恩大学登堂入室以降,并非一成不变地停留在对梵语语言文学的研究之上。固然语言学的方法始终是坚持的方向之一,但所关注的方向和涉及的层面始终在发生变化。现代语言学(Linguistic)的创始人索绪尔在教授了十年梵语的基础上,不断对语言之实质的思索,终于从对Bopp的比较语言学的批评而迈入了语言研究的新时代。上文提及的Max Müller把眼光从对语言的关注,而投向比较宗教学,把德国浪漫主义的思潮镶入了他对吠陀神话的阐释中。
敦煌藏经洞
斯坦因 摄(1907年)
19世纪末20世纪初,探险家的脚步踏入了新疆。美国人鲍威尔(H. Bower)、法国人格勒纳(M. Grenard)和德兰(Dutreuil de Rhins)以及英国人从中国新疆地区收获了数量颇丰的婆罗谜文书和佉卢文书写本,英籍匈牙利探险家斯坦因1900年在和田一带的探险挖掘,终于使德国的东方学者再也沉不住气了。1902年在德国汉堡举行东方学者会议,这次会上成立了国际中亚及远东探险协会。从这一年起,到1914年,德国探险队四次来到吐鲁番地区进行发掘,发现了大量古代多种文字的写卷。这期间,更有斯坦因、伯希和对敦煌藏经洞所藏文书的劫掠。来自中国新疆、敦煌的丰富古代写卷,再一次为欧洲的学术注入了活力。上世纪初在丝路沿线所发现的17种文字,24种语言中,欧洲学者发现了三种已经消亡的古代语言,这就是属于伊朗语族的和田塞语、粟特语,以及吐火罗语。在现代中国,经过现代媒体的渲染,这些名称似乎已是尽人皆知。然而当初破译这些无人知晓的语言绝非易事。欧洲的学者为此付出了巨大的艰辛。若是没有近一百年来语言学方法的确立,没有充分的对梵语文献的掌握,要破译新疆、敦煌发现的崭新而古老的语言是无法想象的。对上述这些陌生语言的破译再一次证实,自19世纪初建立起来的印度学、语言学,不但是人类不可或缺的学科,而且所建立的理论和方法是行之有效的。从一方面看,来自新疆、敦煌新发现对于20世纪之初的欧洲学术界补充了新的能量,而从另一方面,在上世纪初因新材料而立的新学科,例如中古伊朗语等,如何不是欧洲学术传统的扩展呢?
德国 哥廷根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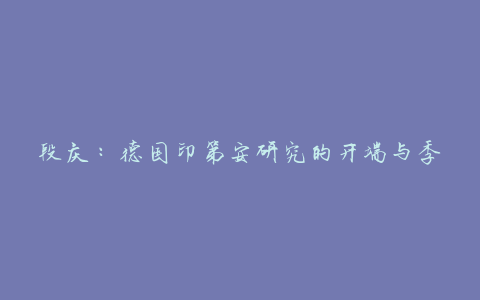
关于哥廷根大学印度学的传统,季羡林先生写过十分精彩的描述,称这里是“梵学天空,群星灿列”。在这些真正伟大的学者之中,基尔霍恩(Franz Kielhorn)驾轻就熟于印度传统梵语文法,他著述的梵语文法至今为深入学习梵语者所推崇。奥尔登堡(Hermann Oldenberg)是巴利语的专家,最早根据巴利文献把佛陀的事迹介绍给德语读者的欧洲学者。他的继任,西克教授正是专攻吐火罗语的专家。西克教授的继任是以研究新疆出土梵文写卷著称的瓦尔德施密特(Ernst Waldschmidt),季羡林是后者的第一名博士生。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了。
[德]恩斯特·瓦尔德施密特
Ernst Waldschmidt
1897-1985
德国印度学、语言学的传统,好比是一片沃野,而受到命运牵引来到这里留学的年轻的季羡林,好比是移栽到这沃野之上的一棵树。经过一番“死抠语法”的学习,“德国式”语言学教学方法,当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时,已经把德国的学术传统植入自己的学术理念之中,德国的印度学传统似乎已经融入他的血液之中,为他未来成就的学术之厦,奠定了基石,而正是沿着这条发端于德国哥廷根大学的道路,他走过了自己的学术生涯,自始至终不曾舍弃。
季先生回国后,着陆在时局动乱、贫穷的国土。失去滋润了语言学的那片天地,似不可能再继续十年负笈所学,不可能继续欧洲式的纯粹语言学研究。除了时局动荡,改朝换代等诸多政治的、环境的因素之外,那套滋长于欧洲的纯粹学术,毕竟不合于中国的土壤。于是他努力寻找着自己的方向[3]。
关于当年的困顿,季先生写道:“我虽对古代印度语言研究恋恋难舍,却是一筹莫展。”(《季羡林自传》,第72页)他在寻找着自己学术的出路。实际上,季羡林先生在中国为自己的学术发展寻找出路的同时,也在寻找中国印度学之趣向。印度学在中国的发展,注定要与在欧洲的发展有不同的方向。
梵文《法华经》写本残片
旅顺博物馆藏
中国的学术界历来有西学中用的传统。而中国文化曾经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中国印度是近邻,印度文化之风早在吹入欧洲一千多年之前,就已经吹遍华夏,对中国的文学、艺术、哲学产生了深刻影响。来自印度的文化之风经华夏人士接受吸纳之后,所创造的文化辉煌,是印度文化于19世纪对欧洲文学、学术发生之影响所不可比拟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翻译的印欧语系语言文献,正是以印度古代语言为主要载体的。自后汉以降,直到宋代,历朝历代从梵语等翻出的佛教经典,可谓浩瀚无量,加之以中国典籍对于古代印度的相关记载,这些是中国印度学取之不尽的源泉。这正是西方的印度学与中国学术接壤的大有作为之处。
通过一番寻找,季羡林先生终于在中印关系史和比较文学史两个领域找到了学术的安身立命之地。这样的寻找,这样的归宿,并不属于季羡林先生个人。作为中国印度学的缔造者,季先生以自身的实践也为一个新的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可能性找到了方向。至今北京大学南亚系古代方向,依然有中印关系史的招生方向。而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应该说已经成为北京大学的特色专业之一。
玄奘三藏像
绢本着色,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在不能从事古代印度语言研究的日子里,季羡林先生开始了在比较文学史、中印文化关系史、佛教学领域孜孜不倦的探索。然而在这些领域,贯穿于季先生学术著作之中,始终有一条清晰的脉络,这就是印度学的基本功,语言的基本功。翻阅季先生的这一类文章,几乎在每一篇都可以找到语言学的踪影,可以找到以语言词汇为依据的论证。在佛教领域,他把对语言的研究成果应用到印度佛教史的研究上,以此探讨对中国佛教影响深远的大乘佛教起源问题。针对如何开展佛教研究,他强调掌握多种外国语言的必要性,认为不懂外文,无法进行佛教史的研究。得益于语言学的基本功,他揭示出中国文学中印度文学的踪影。他可以运用梵语的知识,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正史中找到印度的传说。他甚至凭借吠陀语的功底,为饶宗颐的相关文章以及赵国华所著《生殖崇拜文化论》补漏。他的关于中国丝、纸外传的文章,弥补了中外交流史中只来无往的缺憾,而其中利用语言词汇作为论证的手段,无不达到令人信服的效果。甚至为撰写一篇小小的短文《名言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和宝贵的文化遗产》,他也可以信手拈来,用英、德、法三种语言告诫人们时间的宝贵。
《金刚经》梵文写本
约六七世纪的桦树皮抄本
挪威邵格延(Schyen)藏品
古代语言成为季羡林先生揭示历史的契机,使他能够见他人之不能见,获得独树一帜的原创性发现。众所周知,季先生不但掌握梵语而且是世界上鲜有的几个能看懂吐火罗语的专家,《吐火罗语的发现与考释及其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一文体现了他基于语言的认知。从对比汉译佛经中几个音译词的变化入手,季先生说明:“最早汉文中的印度文借字都不是从梵文译过来的,而是经过中亚古代语言,特别是吐火罗语的媒介。”(《季羡林文集》第四卷:中印文化关系,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51页)他强调吐火罗语的重要性,因为曾经流行新疆地区的一种胡语,与中国文化本身有密切的关系。
仅从刚刚述及的论文来看,季先生治学的一些方法是我们应牢记于心的。佛教传入中国,留下了丰富的遗产,传入的过程跨越近千年。这在一方面是好事,但是也容易令人产生错觉,忘记一个现象与另一现象之间相差的时间差距。汉译佛经集成时间跨度,不同时代译出的经文对一些词语的解释往往相距甚远。例如贤劫千佛的末佛在竺法护的笔下号“涕泣”,而在唐代,则变成了“爱乐”。这其中并不存在孰对孰错,所谓晋代“讹也”,实则是谬判。这是因为竺法护见到的原本,并非纯梵语写卷。在对汉译佛经展开研究时,如果没有历史的时空观念,其实很容易闹出关公战秦琼那般笑话。季先生运用了他丰富的语言学知识,揭示了我国新疆地区曾经的那些古代民族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承载的重要角色。他的独到见解,将随着更多原始资料发现,研究的深入而更显出其意义。
吐火罗B语木简
照片源自新疆龟兹研究院
然而,依我之见,老先生最卓越的学术成就,依然在对古代印度语言的研究以及吐火罗语的研究领域。老先生的学术巅峰作品,轮不到我这学生辈的去评价。我只能说,他的一些著作会再历百年而仍然有人捧读。这里仅和读者交流一些感想。再度翻阅老先生的一些作品,难免感叹发自心底:老先生是真正的国际学者。每当老先生以印度古代语言为论题时,老先生心中的读者众随着他的论证跃然纸上。《中世印度雅利安语二题》、《三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等文章,虽是汉语撰写的,但老先生心中的读者众实际上是那些国际学者。只要触及这样的题目,老先生似乎又回到了哥廷根的那片天地。最有趣的还是读他的《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之书,这里可以体会两种写作风格。汉语写作部分,季先生着意为中国的读者群写作,在导言中详细介绍了吐火罗写卷在欧洲的情况,新的写本在新疆的发现过程,以及弥勒信仰在印度、中亚和新疆的传布。而英语撰写部分,依然是他在德国时养成的风格,直入主题,直接解决问题,而无需多余的话。能使用两种不同的风格面对两个不同的学术群体,这是因为季先生了解中国学术圈的水平以及所关心的问题所在,也了解世界相关学术领域的水平。唯有处于中外两个不同学术世界之水平之巅的人,才能游刃于两个世界。写作时心中装着读者,这是我们应当向他老人家好好学习的写作方法。
季羡林先生手持吐火罗文残卷
季羡林先生以他丰富的译自梵语的翻译作品、丰富的学术著述,最终诠释了中国印度学的范畴。中国印度学,包含了对印度古代语言文学文献的翻译和研究,对印度古代语言的研究,对中印比较文学、中印关系的研究。他同时以对吐火罗语的杰出贡献而成为中国西域古代语言研究的引路人。他强调对中国新疆古代文字研究的重要性。曾经生活在新疆丝路沿线的古代民族,是与中国文化的发展密不可分的。季先生的真知灼见,把中国新疆地区的文化发展从印度学的概念剥离开来。这样的剥离具有科学的意义。无论过去的欧洲学者,还是在中国学术界,习惯把对古代新疆语言文字的研究,视作印度文化发展的一部分。这样的观念的形成,是因为学者对于新疆地域语言文化发展的认识停留在表面层面上。例如,上世纪初期的欧洲学者,针对丝路北道、南道婆罗谜字体的不同形式,提出“斜体笈多”、“正体笈多”的划分方法。后来,经过季羡林先生的师妹,著名Lore Sander博士对中国新疆一带所使用婆罗谜字体的实质性考察,修正了过去的观念,认为“笈多”的印度特征,掩饰了新疆地区的字体有其独立的发展之脉络的特征,因此是不正确的。唯有对新疆古代语言文字有深入了解和研究者,才能认识到新疆古代语言文化发展沿革的真面貌,把对新疆古代文明的研究作为独立的学科来建设。
季羡林先生对中国印度学、西域古代语言文化的贡献,还体现在对学生始终如一的厚爱之上。在对学生的培养上,他显示了博大的胸怀。
写到这里,无法再以论述的模式继续。当我应邀撰写此文,再一次从书架上搬下季先生丰厚的著述,再一次感叹这位老人一生的勤奋时,一些回忆不由得浮现在眼前。季先生一生笔耕不断,他用笔记录下对学术、对人生的感悟。我一直认为,不要再说什么、写什么来评价季先生的一生,因为老人对自己一生所作所为已经写下尽可能翔实的文字。季先生从不看他人写自己的文章,不喜欢他人对自己的溢美之词。更何况作为学生,我有什么资格来评价自己的老师呢?然而,浮现在眼前的回忆让我感受到季先生在学术方面曾经有过的孤独,他的坚守,他的理念,他的规划,他的部署。
《梵文基础读本》
[德国] A. F. 施坦茨勒 (A. F. Stenzler)
季羡林 译, 段晴、范慕尤 续补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清晰的记得,在北大的梵语第一堂课,季先生为我们引见蒋忠新老师,称他是最优秀的学生,隆重地把教授梵语的任务,拜托给蒋老师。我们用的教材,正是季先生根据德文教材编译的。学生时代,我们有事没事,跑到季先生家,当谈起新疆的那些古代语言,先生立刻坐不住了,弯下腰,蹲下去,从书架底层抱出几本厚重而大的书,翻弄着,爱不释手。记得跟随季先生重返德国,他与邀请方谈判,为我争取到赴德留学的奖学金。记得回国后,向季先生报到时老先生高兴的模样。我陪着季先生在临湖轩旁的小路上快步如飞地行走,他嘱咐我要安心学校的工作,教授梵语,并且要在于阗语研究领域做出成绩。记得季先生为我出主意,说最好按照“德国式”教学生,讲述他当年在德国是如何学习的。记得终于在国外发表了论文,把论文交给季先生,他高兴地翻弄着,逢人便夸赞。记得他研究新疆发现的吐火罗语写卷,十分兴奋地告诉我,他发现、确定了50多个吐火罗语词汇。想想我自己每新确定一个于阗语词汇,均认为是个大贡献而沾沾自喜的心情,可想老先生在为吐火罗语研究做出重大贡献的同时该是多么自豪而高兴啊。记得为新疆新发现的胡语残卷的事情在医院里最后一次拜见季先生,他嘱咐着,告诉我“星星之火”的比喻,把传授梵语、巴利语的事业反复叮嘱。记得他一双老眼,已经看不清楚人的模样,仍然摸索着,依然流利地用笔亲手为我们撰写了最后一封信……。这样一位中国的印度学的创建者,对中国的西域研究,对中国的比较文学、佛教等诸多领域做出过卓越贡献的学者,这样一位为培养人才倾注了心血的导师,难道不该被我们好好纪念吗?
北京大学东语系1946年选修课程表
不能不写的是,季羡林先生为中国印度学的建设,经历了痛苦的过程。所谓痛苦,表现在他自己的探索过程,以及中国学界的不接受的过程之中。原本是欧洲学术,移植到中国的土壤,难以适应中国的环境。毕竟,中国人绝不会体验欧洲人于梵语发现了远亲那样的激动。季先生本人经历了探索和拓展的过程,最终能以丰硕的成果成功地走完了自己的学术生涯。而中国学界的发展在新中国之后也经历了重建的过程。至少在东方语言文学领域,学术为何物,鲜有人知。东语系的成立是因为国家需要外交人才。抛开政治背景不谈,对学术的无知,实际上集中体现在文革时期。季羡林先生亲自教过的学生把梵文教材摔在他的脚下,东方语文学的“小将”抄家等行为,对学术的无知,在文革期间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季羡林 《罗摩衍那初探》
外国文学出版社,1979年
文革之后,中国学术的重建时期终于到来。1978年,大学恢复研究生招生,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也招收研究生。那一年,我报考北京大学德语专业。在口试的现场,第一次见到季羡林先生。经严宝瑜、赵林克娣先生推荐,我成为季羡林先生的硕士研究生。季羡林先生的首批硕士研究生还有任远。季先生指定我们学习的课程就是梵语。梵语课在春季开班,梵文课程全部由蒋忠新教授。第一班同学中有任远,胡海燕,还有新疆来的两名进修的同学,其中一名是维吾尔族人。同学中还有两名来自朝鲜的留学生。1979年,南亚研究所再次招生,王邦维、葛维钧成为季先生的研究生,蒋忠新老师再次开班,教授梵文。后来,他们很快赶上我们的进度,可以和我们一起上阅读课,和78年的硕士研究生同一年毕业。
季羡林先生
1980年,季先生受德国Naumann基金会的邀请,重返德国。同行的有社科院从事德国问题研究的郭关玉先生。季先生提出带我随行。作为学生,能随老师访德,我真是无比兴奋。这一次,季先生帮助争取到Naumann基金会的奖学金,并委托哥廷根大学的Bechert教授为同样有德语基础的胡海燕争取到奖学金。1982年,在季先生的支持下,胡海燕赴哥廷根留学,我赴德国汉堡,按照季先生的规划,拜在伟大的伊朗语言学者Emmerick门下攻读博士学位。
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印度学也比初创期有了大的发展,季先生教过的学生在各自的领域有所建树。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所长的黄宝生先生,带领中国通梵语者完成了印度大史诗之一《摩诃婆罗多》的翻译。北京大学梵巴专业已经可以完成从本科到博士的教学科目,已经开展起对西藏收藏的梵文贝叶经的研究,对新疆发现的多种语言残卷的研究,从巴利语直接译出的《长阿含经》也将在今年面世。在季羡林先生去世一年之际,我们隆重纪念季羡林先生。我们将牢记老先生的嘱托,老先生的教导,学习老先生的治学精神和方法,把老先生开创的中国印度学和西域古代语言文化的研究发扬光大。
注释:
[1]参阅Foucault 1973。在这部书中,福柯多次阐述他的理论,例如第207页:“Philology, biology, and political economy were established, not in the places formerly occupied by general grammar, natural history, and the analysis of wealth, but in an area where those forms of knowledge did not exist, in the space they left blank… The object of knowledg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s formed in the very place where the Classical plenitude of being has fallen silent.” 语言学,生物学,以及政治经济学,并非取代了“一般语法”、“自然史”和“对财富的分析”的地位,而是建立在它们所遗留的空缺处……。构成十九世纪认知客体的地方,是古典的五花八门静默不语之处。——笔者译。
[2]1882年,Max Müller 曾在剑桥大学做了关于印度的报告。其中有这样一段话:“But this, though it is taught now in our elementary schools, was really, but fifty years ago, like the opening of a new horizon of the world of the intellect, and the extension of a feeling of closest fraternity that made us feel at home where before we had been strangers, and changed millions of so-called barbarians into our own kith and kin.” “但是这一点,尽管现在连我们的小学都在教,却在50年前千真万确地犹如展开了一道智慧世界的新的地平线,犹如是我们最亲密的兄弟情感的延伸,把几百万本来被称为野蛮的人变成了我们的亲属。” Max Müller reprinted 2007 p. 21.
[3]这里应补充说明,季先生当年的博士论文以混合梵语为研究课题。这一课题在当年欧洲、美国的印度学领域是崭新的。后来,美国学者Edgerton继续在这一领域开拓,基于混合梵语的《妙法莲华经》、《方广大庄严经》等几部佛经,编写出混合梵语词典,以及语法。季先生的博士论文也为Edgerton所引用。从纯粹西学的角度,季先生是为数不多的得到西方学者引用的中国学者。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