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高原的隆起,是地球数百万年来最伟大的巨变之一。群耸的雪山中发源的汩汩细流,最终汇聚成江河浩荡而下,滋养了全球近三分之一的人口。从长江、黄河到澜沧江,这些江河在不同的区域,被不同的民族冠以“母亲河”的称谓,而这三条江河发源的区域,被称为“三江源”。
作为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三江源是高原生物多样性最集中的地区,素有“高寒种质资源库”之称,为众多青藏高原特有物种和珍稀濒危物种提供了栖息地,是雪豹、藏羚羊、野牦牛等高原生灵的重要庇护所,也是我国的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
《三江源国家公园自然图鉴》这部区域性图鉴,涵盖了哺乳动物、鸟、两栖动物、爬行动物、植物五个主要部分,收录了国内众多保护工作者、生态摄影师及国家公园牧民监测员的大量生态摄影作品,展示了这片神奇而壮阔的土地上的缤纷生命,其中收录的近几年三江源新记录到的豹、豺等物种,更体现了三江源最新的生物多样性监测成果。
以下内容经出版方授权节选自《三江源国家公园自然图鉴》一书引言部分,较原文有删节修改,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文中所用图片除剧照外均来自本书。
《三江源国家公园自然图鉴》,王湘国吕植主编,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编著,译林出版社,2021年12月。
在电影《白日梦想家》的结尾,一路寻找25号底片的男主角找到了那位著名的摄影师,当时后者正在等待抓拍一只雪豹。但是当雪豹出现的时候,摄影师并没有拍摄,男主角问他打算什么时候拍,摄影师说:有时候我不拍我喜欢的画面,相机会让我分心,我只想沉浸在这一刻。
这和彼得·马修森的《雪豹》那本书的结尾很像,当他和乔治·夏勒博士历尽千辛万苦走到目的地水晶山的时候,他瘫坐在寺院的前面,这时候当地人问他:
“你来做什么?”
“找雪豹。”
“那你找到了吗?”
“没有。”
“那岂不是妙极了。”当地人说道。
电影《白日梦想家》(2013)剧照。
01
藏族文化中的神山圣湖体系
是极其庞大的
长江、黄河、澜沧江发源地的县城,分别是治多、玛多和杂多。藏语里,“多”是源头的意思,因此,治多,就是治曲的源头。同样地,玛多,就是黄河——玛曲的上游。在黄河源头的扎陵湖和鄂陵湖,你可以见到巍峨竖立的牛头碑,这是黄河源头的象征。
杂多,就是澜沧江源头——扎曲的上游。如果你正在计划一次澜沧江—湄公河的溯源之旅,你会发现这条河流有两个源头,在当地,它们被称为地理源头和文化源头。从地理的角度来说,河流“唯远为源”,但是当地人和这条河流生活了数千年的时间,他们也有属于自己的理解。
澜沧江源昂赛峡谷。
澜沧江的地理源头在吉富山,而文化源头,则在距离地理源头30多千米的扎西齐哇。在藏语里,这是吉祥的水源旋转汇聚的意思。扎西齐哇是由终年不会干涸和结冰的泉眼汇聚而成的湖泊,四周满是当地的人们放置的经幡和玛尼石。湖水荡漾,经幡摇曳,你站在那里,会感到额外的殊胜。
玉树州杂多县扎青乡吉富山。(徐健/摄)
在江河的源头,水不仅仅是以河流的形式出现的。在很多的泉眼或者湖泊的周边,你会经常看到经幡或煨桑的白塔,这是为了祭祀水神“鲁”。
河流和水源中居住着神灵,你如果污染了水源,或者做了不敬的事情,就会得罪神灵。在传统中,人的身体和自然中的元素紧密相连,比如你身上长了水痘,那就是因为水神“鲁”不高兴了。
一条河流,因为这样的寓意,好像就有了生命和形象。
夕阳中水畔的经幡。(彭建生/摄)
这里也有很多著名的山峦,山峦上住着山神。在传统文化里,山神是以山为地标的拥有固定地域和祭祀圈的地域保护神,山神的寄居之处通常是一个村落或者部落所在的山川之巅。在三江源,有阿尼玛卿和尕朵觉悟两大神山,除此之外,还有喇玛闹拉、年保玉则、乃邦等区域性、部落性的神山。
藏族文化中的神山圣湖体系是极其庞大的,和山神、水神联系在一起的,是对山和水的敬畏。祭祀山神和水神,不仅仅是与山神和水神的对话,也是人类在严酷的自然条件下的不断试探。山神和水神,是人与自然在这片土地上美丽的融合,是对不可知的未来和不可控的外部环境的寄托。
02
无法回避的话题:
人兽冲突
动物在这片土地上扮演着不一样的角色。
在藏族人的传说中,他们是罗刹女和猕猴的后代。传说有一只猕猴,受观世音菩萨的点拨,在山南的山洞中修行,最终和罗刹女结为夫妇,生了六个孩子。随着孩子越来越多,采摘的食物不够,猕猴跑去找观世音菩萨,拿到了食物的种子。猕猴们从树上慢慢下来,学会了站立、行走,随后尾巴也变短了。这个从现在的进化论角度来看颇为科学的故事,最早出现于公元14世纪。
历史上,很多民族都会将动物作为图腾,或者在自己和动物之间构建某种联系,以期获得神奇的能力。列维—施特劳斯有一本《猞猁的故事》,描述了在北美印第安人的文化中猞猁善变的形象,及其被赋予的特殊法力。在三江源,猞猁是医者的寄魂体,它高耸的耳尖犹如药囊,散发着药味。
嘉塘草原上的猞猁。(日代/摄)
在如今的阿里地区,吐蕃王朝之前整个青藏高原最灿烂的象雄(汉语称之为“羊同”)文化,把大鹏鸟作为自己的图腾,如今大鹏鸟仍然在整个藏族文化中有着非凡的意义。冈仁波齐山神最早是以白牦牛的形象降落在山上,最后被莲花生大师所降服,成为整个西藏的护法神。三江源年保玉则区域流传着一个故事:一个牧人救下了一条白蛇,白蛇是山神的儿子;为了感谢牧人,山神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而山神女儿的化身就是一头白牦牛。牧民的儿子和山神的女儿生下了三个孩子,发展出后来的上、中、下果洛三部。
藏族文化对白色有特殊的尊重。雪山的颜色,塑造了这个民族对美和庄严的选择,因此雪豹自然也有了更多的寓意。严格地说,雪豹的颜色更接近高山裸岩,它一动不动地藏在岩石中的时候,仿佛是一块石头,但它跳跃的时候,仿佛是岩石间的一颗流星。
雪豹、兔狲和猞猁在传说中是三个兄弟。三兄弟的父母死得早,于是兔狲作为大哥,负责照顾两个弟弟,自己的营养不够,只能长成矮胖的武大郎般的模样;雪豹是老三,从小娇生惯养,整天一副“高富帅”的样子;而猞猁作为老二,被关注得很少,会主动让自己没有存在感,神出鬼没,性格孤僻。
长江源头的三只小兔狲。(韦晔/摄)
在藏族的文化中,狗通常是家族中重要的一员。在传说《阿初王子》中,王子看到人们因为食物不足而饱受饥饿之苦,决定去蛇王那里偷种子,但蛇王发现了他,于是把他变成了一只狗。阿初王子逃跑之前,在青稞堆里打了一个滚儿,浑身沾满了种子。在蛇王的追杀中,王子越过山川,身上的种子都被水冲走。黎明时分,当阿初王子跑回原来的王国时,人们惊喜地发现,王子竖起的尾巴上,还沾着最后的种子。于是,人们靠着这颗种子开始种植青稞,从此过上了富足的生活。因此,当三江源面临如今不断变化的流浪狗的问题时,我们需要评估它对生态的影响,也需要评估它对传统文化的干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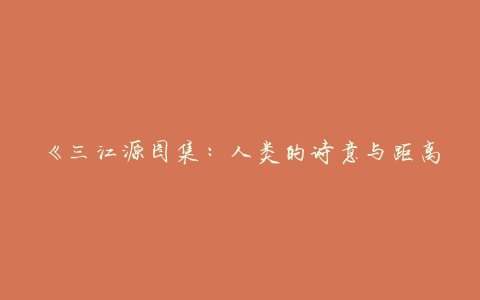
回到当下,人兽冲突是在三江源无法回避的话题。从雪豹、狼捕食家畜,到棕熊扒房子,你总是会听到人们用各种各样的语言来阐述这些问题。现代的研究者们一般认为人类与大型食肉动物之间是竞争的关系,两者对空间、食物等自然资源的竞争导致了人兽冲突,因此通常建议通过约束竞争或促进生态位的分化来缓解冲突、实现共存。
在昂赛进食牦牛的雪豹。(武亦乾/摄)
然而,竞争和对立并不是这片土地上人与野生动物关系的全部。从当地很多人的视角来看,虽然雪豹会吃家畜,但牧民和雪豹之间的关系并非竞争。任何事物都是因为各种条件的相互依存而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冲突并不是共存的对立面,只是不断变化的背景下共存的一种表现形式。
03
大家都依靠草地来生存
在三江源,草场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大约在8000~10000年前,青藏高原的人类开始驯化牦牛;牛羊等家畜取食于草场,把植物转化成肉制品和牛奶等蛋白质,青藏高原的游牧民族由此得以生存。由于草场和家畜在牧民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牧民对植物也总是会有特殊的感情和认识。一种植物的藏语名字,往往融进了时间和物候,还有牧民的期盼。
比如矮金莲花也被叫作“治果色迁”。“治”是母牦牛的意思,而“果”是奶汁最多的时候。这个名字是想说,当矮金莲花开花的时候,母牦牛的奶会变多,酥油会从之前偏白的颜色变成黄色,可以在早上和上午11点各挤一次牛奶了。矮金莲花在这里成为物候的一个指标,随着它的盛开,万物复苏,草地的营养恢复,母牦牛的奶也渐渐多了起来。三江源的冬天狂风肆虐、大雪纷飞,人们往往只能窝在家里。度过了一个漫长的冬季,当看到矮金莲花开花,迎来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的时候,牧民将欢喜全都寄托在这小小的黄花上。
矮金莲花。(牛洋/摄)
植物很多时候也会被作为供奉山神的祭品,比如大果圆柏会被用来煨桑,白烟缥缈,香味四溢。很多年老的圆柏也都会被绕上经幡,人们认为会有神灵依附其上。因为所有的土地都是有神灵和主人的,所以在人畜不兴旺时,需要将四种植物放在四周,以使土地神喜悦:东方放柏树,西方放高山绣线菊,北方放柽柳,南方放窄叶鲜卑花。
华西贝母倒挂的花很像一只铃铛,它又喜欢长在冷凉湿润的地方,跟神灵中鲁族的生活环境很像,因此在藏语中被称作“勒都珑子”,意为鲁族的风铃。鲁族作为掌管地下的神灵,主要生活在有水的地方,它们拥有大量的财宝,也拥有很强的法力。蛙、蟾、蛇等都属于鲁族的成员,任何污染水源、伤害鲁族生灵的行为都会受到惩罚。
还有狼毒,在生态学上它或许是草地退化的某种标志,但在传统的藏族文化中,它的根可以用来做纸。狼毒的根有毒,做出来的纸不会被虫蛀,所以会被用来印经书或者藏药典籍等重要的书籍。
白扎林场盛开的狼毒。(李磊/摄)
在三江源,无论是野生动物还是人类,都依靠草地来生存。为了适应高寒的生态环境,这里的人们采用了以游牧为主的生产方式。牧民会随着季节的变化逐草而居,暖季上高山牧场,即“夏牧场”,冷季转移到低洼牧场,即“冬窝子”。如此一来,不同区域的草场就得以休养和生长,家畜又可以很好地利用处于生长期的牧草。但如今,由于牧民对现代化生活的需求,以及定居、围栏等政策的引导,游牧正在慢慢减少,并深度地影响局部的草地。
隆宝正在进食鼠兔的藏狐。(左凌仁/摄)
04
人类并不被认为是独立存在的生命
在藏族人的传统文化里,上空是拉域,地表是念域,地下是鲁域。拉、念和鲁是民间崇拜的古老的原始神灵。在藏族人的世界观里,除了人之外,还有超自然的神灵和鬼怪,它们以附于自然实物的形式出现,形成了从万物有灵发展出来的完整的神灵体系。
除此之外,情与器,即生命与环境的关系,也是传统文化一直以来不断辩论的关键问题。有一种直观的看法认为,外器是支持者,而内情是被支持者,没有了容器就无法承载内容物。换言之,没有环境就没有生命。这种看法近似于“没有合适的栖息地,物种就无法生存”。
与之相对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外器是被支持者,内情是支持者,先有生命才有与之相应的环境,也就是说,先有物种,才有适合于它的栖息地。比如黑颈鹤是在雪域高原上生长繁殖的唯一鹤类,属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对绝大多数自然保护者来说,栖息地的丧失和退化是造成目前全球物种数量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湿地的干涸导致黑颈鹤的离开”,这才是惯常的逻辑;但是很多老人坚持认为,是黑颈鹤的离开导致湿地干涸。前一种想法强调的是外部环境对生命的决定作用,而后者强调的是生命主体的能动性。
湿地中繁殖的黑颈鹤。(左凌仁/摄)
每个生命的行为会影响到它所处的外部环境。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许多当地的知识分子会认为,当前面临的环境问题本质上是人心的问题,因此环境保护的关键在于改变人心。
与将人和自然区别对待的西方文化不同,世界上许多地方的传统文化往往更全面地将人视作自然的一部分。在某些传统文化的世界观里,人类并不被认为是独立存在的生命,而是“生物社会复合体”的组成部分;野生动物并不是完全受环境或本能控制的无意识的生物,而是具有主观能动性,并通过轮回、狩猎、寄生等方式与人类共同处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行动者。
我们可以尝试想象,三江源的每一个生命个体——包括人和非人的动物都在构建各自的主体世界。这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当地人如何看待自然,包括山水、动物和植物,以及如何看待与它们的关系。
寺前的旱獭。(何海燕/摄)
青藏高原的高海拔、稀薄空气、充足的日照及冰雪狂风,构成了这片土地独特的环境特点,同时也影响着这里人们的生产结构、生活方式和饮食文化。如果你开始在这片土地上旅行,我们希望你可以了解这里的衣食住行。
三江源是以畜牧业为主体的区域,兼顾少量的农业。畜牧业以饲养牦牛、绵羊等为主,而农业生产主要是种植青稞、土豆、芫根等。
在这里,你有机会看到岩画。这里面的野生动物及与之相关的狩猎文化,曾经在三江源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玉树很多地方的岩画,都表现了三江源早期的狩猎历史与文化;透过这些岩画,我们可以看到远古时代盘羊、白唇鹿乃至豹和人类的互动。
玉树曲麻莱塔琼岩画。(尼玛江才/摄)
你也可以尝试穿上一件藏袍。藏袍具有腰襟阔大、袖子宽长的特点,面料包括棉布、绸缎、氆氇。在三江源区域,藏袍曾用水獭的皮毛来防水和做装饰,在服饰的改良和保护工作的影响之下,如今动物的皮毛已经被彻底地替换。男性的袖子要比女性的长很多,那是因为男性不需要做那么多细致的工作,并且经常在外奔波,着长袖便于保暖。
如果你住在牧民家,那么糌粑会是传统的主食,它和内地的面不一样:面通常是将小麦磨成粉之后,再煮熟和炒制;而糌粑是把青稞翻炒熟之后,再进行磨制。在牧民家里,你可以吃到青稞粥、芫根、面饼和肉。随着运输条件的改善,如今牧民也会买很多的水果和蔬菜,饮食习惯也趋于多元化。在牧区,一般早上吃糌粑,中午吃米饭和炒菜,晚上吃面片。糌粑、米饭和面,三种主食一样不少。
牧民家传统的房子多以夯土作为墙体的结构,然后加上石头屋顶,窗户一般比较小,这是为了保持温暖。你如果有机会参观藏传佛教寺庙,会被这些恢宏的建筑所震惊。藏传佛教的寺庙通常会有不同的颜色主体,比如萨迦派的寺庙会呈现出红、白、黑三色,这是代表文殊、观世音和金刚手三位菩萨。藏传佛教寺庙房顶的檐瓦之下,经常会覆盖一层染成红色的金露梅枝条,很是漂亮。
果洛州玛可河林场的传统藏式房屋。(左凌仁/摄)
这里的道路,自然还没有非常顺畅,所以,你需要接受颠簸和崎岖;但路上的风景,或许可以帮助你忘却这些不适,窗外偶然遇到的动物,会成为这一路的惊喜。
本文经出版方授权节选自《三江源国家公园自然图鉴》。
原文作者|赵翔;
摘编|安也;
编辑|西西;
导语部分校对|郭利。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