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古籍
编者按:数年前金克木先生的一篇文章对我很有启发,至今依然余音绕梁。——翻译教学与研究
大约三十多年前,我住在印度的佛教圣地鹿野苑的招待香客的“法舍”里。那地方是乡下,有两座佛教庙宇,一座耆那教庙宇,一所博物馆,一处古塔的遗址和一段有阿育王铭刻的石柱,还有一个图书室。这图书室里有一部影印的碛砂板佛教藏经,我发现这几乎无人过问的书以后,就动手在满是尘土的一间小屋子里整理,同时也就一部一部翻阅。这只能叫作翻阅,因为我当时读书不求甚解,而且掉在印度古语的深渊中不能自拔,顾不上细读这浩瀚而难懂的古代汉译典籍。可是,我也随手做了一点笔记,取名为《鹿苑读藏记》,当然不过是记给自己看的。那时钻在中外故纸堆中“发思古之幽情”,居然还诌成一首旧诗:
西行求法溯千年,绝域孤征向五天。
万顷惊砂欺衲破,千寻浊浪试心虔。
争知胜业空今古,应有嘉名耀简编。
寂寞何堪尘土里,徒余脉望识神仙。
不用说,我那时的生活和心情都是应当受到批判的。解放后,我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就毫不吝惜地对过去这些告别了。前些年,由于种种原因,早已扔在一边的所谓《鹿苑读藏记》也随同其他故纸一起,被我像送瘟神一样送掉了。当时为了卸下包袱轻装前进,这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不能归咎他人,也无须“反求诸己”。这是实话。
可是,这成堆的古代翻译是不是还会有人看呢?这当然用不着我操心。然而积习未忘,有时不免想到,是不是要有新的《阅藏知津》或“佛藏书目答问”之类的书,好让非宗教信仰者和非宗教研究者也能略知一二?“愿者上钩”,“各取所需”,这样的读者大概需要有一个显示内容的“向导”。现有的各种版本的佛藏都是照各宗派的观点分门别类,各有一套分法,并不依现代知识排列;外行查考不易,内行又少有人为外人指点非宗教的入门之道。索引和词典还不能解决问题,因为书名、篇目、专名、术语等不能说明书的内容。提要如《阅藏知津》又不指示门径次第。我想这些古董大概只有充实藏书楼、博物馆和展览会的作用了。
然而,人类的文化遗产并不能为一个民族所独占,现代各门学术都国际化了。印度的佛教古籍并不只属于印度。巴利语的佛典有泰国、缅甸、斯里兰卡、印度等国字母以至罗马(拉丁)字母的排印本。汉译佛典及其注疏除我国的各种旧版外,还有日本的刊行本。藏译的佛典,《甘珠尔》《丹珠尔》,除我国的德格版、奈塘版、北京版等外,外国也在影印出版(德格版的?)。梵语及混合梵语的原本也陆续不断发现并刊行。
国际上早已知道,有很多古写本现在还藏在我国的西藏和新疆,外国人弄去的只是其中一部分;他们已出版了不少,有些还在逐渐校刊中。做这些工作的并不都是佛教信徒,其中有些是学者,不信佛教,有的人甚至不信任何宗教。他们为各种各样的动机和目的而钻研这些古董。研究宗教典籍的不一定是嗜好宗教鸦片的瘾君子,也不一定是反宗教的人物。
因此,我想,谈谈这庞大的佛教文献未必就是给鸦片做广告吧?假如烟之不存,自然也不必宣传戒烟,可惜这还只是理想。这且不谈,汉译佛经本出在我国,国际上引用的却总是日本的《大正藏》。引书目的前多年也是引用日本南条文雄译的《大明三藏圣教目录》(英文);后来又引用印度师觉月的《中国佛藏》(法文),我总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好像看到我国创始的围棋在国际上用的名称是日本语的GO一样。看到我国的古代、近代、现代的资料在国际上日益成为研究热门,而我们自己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我总觉得不愉快。当然我不是不想要外国人研究,而是觉得我们应当有资格、有权利也参加一份。若是只有自己人干的才算数,别人干的都不算数,那恰恰是宗教教派的狭隘心理。幸而这些年来我国还是有人以科学态度认真研究各种宗教;至于我,对佛书虽经过几十年的隔离,竟还想提起谈谈,那只能说是旧习难除而已。
话说回来,不信任何宗教只信科学而想读佛书(只指汉译),从何下手?我想首先要知道这是长期积累和发展的、有各种不同内容的、复杂的古代文献,译文也是不同时、地、人所出。原文和译文都有许多重复、交叉。据支那内学院一九四五年《精刻大藏经目录》统计,连“疑伪”在内,有一四九四部,五七三五卷;如果把秘密部的“仪轨”咒语等除开不算(一般人不懂这些),就只有一〇九四部,五〇四六卷。欧阳竟无一九四〇年为“精刻大藏经”写的《缘起》中说,除去重译,只算单译,经、律、论、密四部共只有四六五〇卷。这比二十四史的三千多卷只多一半,并不比我国的经、史、子(除释、道外)的任何一部更繁,更比不上“汗牛充栋”的集部了。这毕竟只是印度古书中的一部分。佛教在古代印度也只是其宗教之一,只是其社会文化的一个方面。
宗教信仰是意识形态,但宗教活动不仅是思想和信仰。宗教是一种社会现象;也许可以说,古代社会有某种矛盾,由此有群众性的宗教活动,然后出现了系统化的教理。教会是主要的,宗教的各种社会性组织及活动是宗教的实体。所以宗教的理论教条是后起的,甚至其中有的同它的社会活动历史脱节以至矛盾。与其说教祖创造教义而后建教会,毋宁说是由社会矛盾而兴起教会,由此产生教义与教祖。有些宗教运动并没有系统教理。如果说宗教是教祖个人所创造,仅是极少数人长期愚弄、欺骗大多数人的,恐怕不像是唯物主义说法。
依照上述这一看法,而且历史和传说也是说佛去世以后佛教徒才开几次大会“结集”经典,那么,这些打着佛教标记的文献当然与佛教教会(佛教叫“僧伽”,意译是“和合众”)密切有关。既然如此,它就可以大别为二类,一是对外宣传品,一是内部读物。(这只是就近取譬,借今喻古,以便了解;今古不同,幸勿误会。)不但佛书,其他古书往往也有内外之别。讲给别人听的,自己人内部用的,大有不同。这也许是我的谬论,也许是读古书之一诀窍。古人知而不言,因为大家知道,我则泄露一下天机。古人著书差不多都是心目中有一定范围的读者的。所谓“传之其人”,就是指不得外传。远如《易经》,当然最初只是给卜筮者用的,《说卦》《序卦》也不是为普通人作的。近如《圣谕广训》,大约五十多年前,已经是民国了,我还在安徽的一个小县城听到有人夜间在街道上煤油灯下用说唱故事形式宣讲,仿佛是唐朝的“俗讲”。那书叫《宣讲拾遗》。这可谓普及老百姓之书了。然而皇帝和贵族大臣们自己并不听那一套皇帝“圣谕”,也不准备实行,那些是向黎民百姓“外销”的。这大概是封建社会里的通常现象,中国印度皆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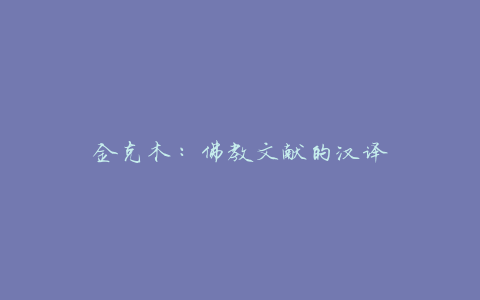
佛教文献中的“经”,大多是为宣传和推广用的。《阿弥陀经》宣传“极乐世界”,《妙法莲花经》大吹“法螺”,其中的《普门品》宣扬“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都明显是为扩大宣传吸收信徒用的。还有丛书式的四《阿含经》《大集经》《宝积经》,甚至《华严经》《般若经》也大部分似对内,实对外。还有“内销”转“外销”的,如《心经》(全名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本来是提要式的口诀,连“十二缘生”都只提头尾两个,可见是给内部自用的;大概因为其中说了“度一切苦厄”和“能除一切苦”,又有神秘的咒语,便成为到处配乐吟唱应用的经文,也用来超度死人和为早晚做佛事之用了。此外,许多讲佛祖传记和“譬喻”故事的,包括著名的《百喻经》,都是对外宣传品。
“内部读物”首先是“律”。各派自有戒律,本是不许未受戒者知道的。原来只有些条文(“戒本”),其他应是靠口传,不对外的。可是有些派别的戒律也都译出来了。晋朝的法显和唐朝的义净还“愤经律残缺”,远赴西天,又求来两派的。一个得来《摩诃僧祗律》,一个得来《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加上另两派的《四分律》《五分律》,以及《十诵律》,都是几十卷的巨著,不但有律文,还有案例。法显、义净译的两部书的梵语原本近年来已发现并刊行了;可惜我没有见到书,不知是否有汉译这样多。这类“不得外传”的书对于现在喜欢文学和历史的读者当然很有意思,可是其中有的部分仿佛是“暴露文学”,确实是“不足为外人道也”。记述佛教内部分裂成为一些山头派别的,除律中的“破僧”事以外,还有《异部宗轮论》(另有两译),也不会是给外人看的。
算在“论”里的一些理论专著,有的实是词典,如《阿毗达磨集论》,或百科全书,如《阿毗达磨俱舍论》。“俱舍”就是库藏,现代印度语中这词就指词典。有的是以注疏形式出现的百科全书,如《大智度论》。有的是本派理论全集,如《瑜伽师地论》。还有类似这两种的,如《发智论》和《大毗婆沙论》。有的是理论专著或口诀,如《解脱道论》(巴利语本为《清净道论》)、《辩中边论》《唯识三十论》《因明入正理论》。有的是内部辩论专著,如《中论》《百论》。有的是专题论文,如《观所缘缘论》。还有两部不属佛教的理论书,《金七十论》和《胜宗十句义论》,更是供佛教徒内部参考了。这些都是有一定范围的读者对象的。著书的目的本不是为普及,所以满纸术语、公式,争论的问题往往外人看不出所以然。“预流”的内行心里明白,“未入流”的外行莫名其妙。
至于秘密部的经咒,本身当然是对内的,而应用却往往对外,借以壮大声势,提高神秘莫测的地位。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所有只供应内部的书,包括以上所说各类,其内容都是不便对外人说的。我不敢说知道,自以为知道的也不敢对外说;“内外有别”,说出来怕会招致“内外夹攻”,何苦来呢?真想知道的自会硬着头皮往里钻,不致无门可入,用不着我多嘴。
佛教文献一般分为“经”“律”“论”三藏,这是就形式而言,循名求实则往往不然。例如《入楞伽经》《解深密经》,实际是讲宗教哲学的“论”,只形式上是“经”。无论为教内或教外,应当有一个经过整理的编目,删芜,去复,分门,别类,标明所崇佛或菩萨的教派,分出各主要哲学体系,不受宗派成见束缚,指出其内容要点,说明各书间关系,列举已刊或待刊的原本或同类的原书以及各种语言的译本。那样一来,全部文献的情况就比较清楚了。然而此事谈何容易。“我佛慈悲”,也许二十一世纪国际学术界会有这样的书出现吧?也许早已有之,而我孤陋寡闻不知道吧?
有一点应当指出,佛教理论同其他宗教的理论一样,不是尚空谈的,是讲修行的,很多理论与修行实践有关。当然这都是内部学习,不是对外宣传的。在“律”中不但讲教派历史,讲组织纪律,还为修道人讲医药。还有用心理方法治疗精神病的《治禅病秘要经》之类,以及一些治病和驱鬼的咒语。这些都是在山林中修道所必需的。当然治病咒语也可对外。出家人生活多半要靠人施舍,所以“布施”列于“六波罗蜜多”之首。佛教也是很讲究实际效果的,否则早就完了,更谈不上流传到印度以外了。至于佛教后来为什么在印度本国消亡而在外国发展,则是另一问题。
这里还想啰唆几句关于汉译佛教文献的语言的话。
说到文体,汉译佛典大部分是六朝和隋唐的,能读那时文章的人不会有大困难。问题在于其术语或行话。任何一行都有行话。若要求所有的书都只讲日常生活口头应用的语言,人人都懂,那样的普及只能取消一切专科行业,也是办不到的。工农商学兵都有自己的行话,宗教何独不然?科学中也是“隔行如隔山”。语言的基本符号单位是词,词各有所指,像数学符号、化学元素符号等一样。不过佛教特别喜欢用各种术语,又喜欢计数,这也是印度习惯。他们的逻辑也是公式化、数学化得很。佛教为超脱死,要追溯生,从成胎到生产的经历都一一计算,仿佛讲产科医学。分析心理越来越细。佛、菩萨称号越来越多。上自天文,下至地理,无不涉及。这真好像是对记忆力抽所得税。可以说是存心不让外行懂的。汉译的译名又不统一,如“观自在”即“观世音”,“五阴”就是“五蕴”,还有时忽译音、忽译义。最难人的是有的印度习惯语也硬搬过来。在玄奘译的一部“论”中(忘记是否《成唯识论》了),忽然冒出一句“天爱宁知……”真是天知道!佛教称一般的神为“天”,即天神。“天神所喜爱的”本是阿育王的头衔,后来却成了一个习惯语,即傻瓜。这句话是作者与对方辩论时动了肝火,说,“你这个傻瓜怎么能知道……”玄奘当年用古汉语照字直译出来就有点神秘莫测了。好在这种地方还是有限的。若是只想欣赏文学故事,倒比读六朝文难不了多少。至于“四谛”“六度”之类不过是简化符号。我们现在不也用“三反”“五反”“整风”“反右”“四化”之类从字面看不明白的符号式的词吗?知道了那一套符号的涵义,熟悉了公式,弄懂佛教语言并没有多大困难。不过要讲哲学和修行要道,明白其中讲的究竟是什么,那还是要花点工夫,好像学数理化和一门外国语一样,急躁不得。当然,若只是要定性,倒也不难。只要判其为主观唯心主义还是客观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还是带有一点辩证法因素,纯粹的信仰主义还是夹杂着一点朴素的或机械的唯物因素,定其历史背景和阶级属性,指出其对劳动人民的欺骗和危害及为剥削阶级服务的反动本质,或则再同杜林、贝克莱、马赫、黑格尔、康德等对对号,都无不可;反正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总是反动、错误、有局限性就是了。如果简单化了去看,什么佛教文献,无非是“满纸荒唐言”,任凭批判,好在印度古人不会还口。
还有一点要说。一九七六年欧洲出了一本《西藏语法传统研究》。由此提出了一个问题:和梵语语系截然不同的藏语如何能应用梵语的语法体系来构成自己的语法呢?我们由此自然会想到《马氏文通》。汉语和拉丁语也是构造大不相同,何以能用拉丁语法的格式讲汉语语法呢?利用印欧语系的语法格式讲汉语的何止这一部?一向我们以为这不过是削足适履,可是帽子总是不能当鞋穿吧?既然说得通,就必有共同之处(不见得就是现代语言学所谓“深层结构”)。梵藏和梵汉的翻译可以作为大量研究材料。
这里说一个例子。梵语有复杂的词尾变化,而汉语却不然;可是梵语的复合词是去掉前面的词的语尾的。梵语复合词越来越长,就越来越像古汉语。汉语直译梵语,不过是割去梵语词的尾巴,而这在梵语复合词中已经如此。再就不复合的词说一个例子。佛经开头一句公式化的“如是我闻”中,后两字中,原文的“我”是变格的“被我,由我”,“闻”是被动意义的过去分词,中性,单数,两词连起来是“被我听到的”。这在古汉语中照原词义和原词序用“我闻”就表达了“我所听到的”,可以不管原来的语形变化。梵语的书面语发展趋势是向古汉语靠近,表示词间关系的尾巴“失去”成为待接受对方心中补充的“零位”(数学用语)或“虚爻”(占卜用语)。同时,由所谓“俗语”转变为现代印度语言的口语发展趋势则向现代汉语接近,性、数、格之类词形变化简化甚至失去,而增加表示词间关系的词。这可以说是语言的历史发展中的有趣现象吧,可惜似乎还不见有人认真做比较研究。
采直译、“死译”或“硬译”方式的汉译和藏译佛教文献中有不同语系的语言对比问题,有翻译中的语言学问题。近二十年来国际上各门科学都蓬勃开展新的探索,可能语言学也会很快把这类研究提出来了。中国人应当更有方便吧?有志之士“盍兴乎来”。——当然要谨防中毒。勿谓言之不预也。
实在不应再谈了。但在佛教文献的大门上,我想还要写上马克思引用过的,诗人但丁在地狱门上标示的话:
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
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摘自 金克木 《怎样读汉译佛典》
End









